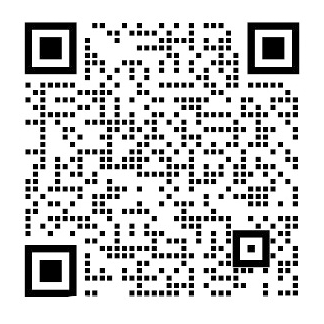文献翻译原文
Extracted from The Hermeneutic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which is written by Radegundis. Stolze. Stolze is a German translator, university lecturer and long-term member of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Germ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The excerpt is from 279th page to 285th page.
1. Developmen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underwent considerable changes during the past years. The scholarly interest shifted from a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differences to the social role of translation in the literary context. At first, translation was defined as an inter-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process with code-switching, so that it was seen merely as an exchange of source language material by target language material (Catford 1965; Kade 1968).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describes relationships of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languages.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not as simple as that.
Later the scientific focus turned to text 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as it became clear that a text is not only an interconnection of semiotic signs, but it contains also aspects from the situation and intention of an auth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translations in a target culture and described various changes, shifts and adaptations for external reasons to be found in translations (Toury 1995; Bassnett 1991; Lefevere 1992). This is not a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basic approach is empirical corpus analysis.
As translations are being done by individuals, there is also a 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ose individuals called translators. Tests are being made and think-aloud protocols are written to find out how creative solutions are found (KuBmaul 1995). This again is not a theory of text production but a description of how translators are thinking, whether this is good or bad. A didactic learning effect is seen in the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results, however without categories of evaluation. The interest is in analyzing the origination of creative formulations that are structur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ource text.
As translation is more than a mere linguistic transfer, and as there should also be evaluation criteria regarding the adequacy of formulations, the question of the translation purpose has been raised. The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or Skopos Theory maintains that the general guideline of translating is its purpose, the question for whom and to which objective we are translating (Vermeer 1996). A translation must be adequate for the addressees and the intended function, and this coherenc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similarity to the source text. Translation is purposeful text production.
It has become clear meanwhile that translating as a human activity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it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inter-linguistic factors. Translation is the work done by a translator who reformulates the message first understood from an original text. The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however, is not seen in the Skopos Theory; it is simply accepted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said: 'A translation is adequate, when it functions' (Honig 1995: 74). This proposition is too unspecific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translation theory.
2. Discourse analysis
First of all there should b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tter of discourse. The question should be raised whether understanding regards oral or written communication. This question is relevant, a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preting as an oral transfer of speech heard, and translation as a written presentation of written text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fortunately this difference is at present not sufficiently seen, let alone made a subject of discussion in cognitive studies. While in speech acts with a shared presence of speaker and audience, speakers may negotiate their text representations with other speakers and listeners; in written texts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specific object from a visual scen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rehension tasks.
According to Sperber and Wilsons relevance theory (1986),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in that speakers negotiate their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an optimization of means and resources. Interpretation of utterances works by the reduction of mental models to minimally relevant schemata, from which information emerges that appears maximally new for the audience. The underlying basic cognitive strategy of all human behavior is the strategy of selecting the most plausible assumption out of the present cognitive environment. This fact results from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people will try to spend as little as possible cognitive processing effort on supply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15) the crucial mental faculty that enables human beings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is the ability to draw inferences from peoples behavior. Relevance Theory applies to “ostensive 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making manifest to an audience ones informative intention”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54). To gain maximally new information, there is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outcome of an act of communication has to modify some previously held assumptions in order to be found rewarding” (Gutt 2000: 28). However, this functions only in oral direct communication, when the speaker and hearer are both present and share the same context of the utterance.
The approach in understanding a written text is totally different, as hermeneutics has shown. It is a great defect of Gutts attempt to transfer the relevance theory on translation, thinking that it would replace any other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 (Gutt 2000: vii). All over Gutts work we read about “text, utterance, spea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文献翻译译文
节选自雷德格迪. 斯图尔斯的《阐释学在翻译的运用》,雷德格迪. 斯图尔斯是一位德国享有声誉的翻译家、大学讲师。也是欧洲翻译研究协会和德国翻译理事会的长期会员。节选了第279页到第285页的内容
- 翻译研究的发展
翻译研究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的学术兴趣从描述语言差异转向了文学语境中翻译的社会角色。 起初,翻译被定义为一种伴随语言转换的语际交流过程,因此它仅被视为目的语材料和源语言材料的交换。 对比语言学描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关联性。然而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
之后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文本语言学和语用学,不难看出,文本不仅仅是符号标记间的互连,还包含着作者的情境和表达意图。 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翻译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影响,同时它也描述了译文导致中外部原因出现的各种变化,转变和适应。 这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理论,而是描述性翻译研究。 基本方法是分析经验语料库。
翻译作品的过程是由个人完成的,因此也有人通过认知分析解析那些可称作“译员”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测试,也在编写协议以研究他们是如何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这也并不是一种文本输出理论,而是对译员思考方式的客观描述。在对结果的批判性讨论中可以看到教学学习效果,但却缺乏评估类别。此项研究的兴趣在于分析这些创造性想法的起源,这些想法在结构上区别于源语文本。
翻译的功能不仅局限于语言转换,同时还缺少与大量创新想法有关的评估标准,因此研究者提出了“翻译的目标”这一问题。功能翻译理论(也称为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一般准则是其目标,想一想我们为谁翻译,翻译的受众是谁。翻译必须符合受众的需求和预期的功能,和译文与源语文本的相似度相比,这一要求要重要得多。翻译是有目的性的文本输出。
同时,翻译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在人类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由语际因素决定的。翻译是译者的工作,译者需先重新理解原文中的信息。然而,在翻译目的论中并没有提到“理解原文”这一要素,它只是作为一种事实为人们接受。Honig提出:“出色的翻译必须是有效的”。这个命题作为翻译理论的基础而言不够明确。
- 语篇分析
首先,研究人员应该对语篇展开调查。 理解是否涉及口头或书面沟通这一问题不能忽略。 这个问题具有关联性,因为口译的过程(口头翻译听到的话语)和笔译(跨文化交际文本语言转化的书面呈现)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过这种差异目前尚未充分显现,更没有在认知研究中成为讨论的话题。 演讲需要讲者和观众共同出席,演讲者可以与其他发言者和听众讨论他们的文本陈述; 而在书面文本中,从视觉场景中识别特定对象是最重要的理解能力之一。
斯珀伯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提出沟通取决于相关性原则,即说话者通过优化的手段和资源来协商他们的理解。话语的解释通过将心理模型简化为最低限度的相关图解来起作用,受众能从中发现最多的新信息。人类行为的所有基本认知策略是从当前认知环境中选择出最合理的假设性策略。这一事实的产生源于人们会花最少的认知处理精力来提供语境信息的这一一般性原则。关联理论认为,让人类能够相互交流的心理天赋是一种能从人们的行为中得出推论的能力。关联理论适用于“明确的推论型交流,其向观众展示一个人的信息意图”。为了获得最新的信息,需要“交流行为的结果必须改变一些先前的假设才算有价值”。但是,当讲者和听众同时出席并共享语篇的相同背景时,这一理论才能在口头直接通信中起作用。
而阐释学理论中展示的理解书面文本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古特尝试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领域的重大缺陷,他认为它将取代所有其他一般性翻译理论。 在古特的所有作品中,我们都读到了“文本,语篇,讲者,作者,听众,读者”等字眼,但他并未提到听力或阅读中认知策略的巨大差异。如果文本翻译被纳入语际交流范畴的话,关联理论也不能简单地适用其中。
而阐释学理论中展示的理解书面文本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古特尝试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领域的重大缺陷,他认为它将取代所有其他一般性翻译理论。 在古特的所有作品中,我们都读到了“文本,语篇,讲者,作者,听众,读者”等字眼,但他并未提到听力或阅读中认知策略的巨大差异。如果文本翻译被纳入语际交流范畴的话,关联理论也不能简单地适用其中。
那译者充当何种角色呢? 译者需向目的语文化读者呈现文本中的信息,以便他们理解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解析。 译者的任务不是为读者详细解释文本信息,而是改写或改编文本,方便读者阅读。 在阅读原始文本时,读者会决定译文是否可接受。
翻译中的一大问题在于译者要翻译的文本是未知的,文本可能取自一个陌生的文化或一个特定的专业交流领域(如法律或医学文本),译者必须为目标读者制定一个专门的文本,这些目标读者大多数并不来自译者的社交圈,如诗歌读者或某些专家。 因此,原始信息和目标读者对译文的期望都受到绑定。 对于这种双重绑定来说,不专业的译者可能会失败。 因此,他们的职业定位和文本处理方法必须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
- 阐释学历史疑问
这是阐释学领域,那么它和翻译有什么联系吗?与其不断描述我们观察到的信息或设计一个客观翻译模型,我们应该转变视角,从译者的角度看待处理译文的方法。我如何理解文本使其适用于目标读者?我的翻译标准是什么?我如何比较译文质量?这正是阐释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讨论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
我简单提一些历史上影响阐释学理论发展的观点。在古代,神谕便是用阐释学的方法来理解的。牧师会理解并解释上帝传达的信息,这是相关的,因为神谕往往决定这人们的生活。之后在中世纪,我们用寓言的方式阐释圣经,正如奥古斯汀阐释的那样,圣经不仅具有文学含义,更有救赎的力量。这需从内心深处感知,并根据天主教教义官方解释。
我们认为的的理解问题只出在现代开端。 印刷技术发明至今,口头交流和官方文本朗读的作用已经丧失,阅读印刷文本获得支持,这与早先的情况有所分离。 由于语言的所有元语言符号正渐渐缺失,因此这些文本不再容易理解了。 现代阐释学则由此寻求规则来证明,不同的读者如何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本书。 假设关键词是“生命的应用”,你可以安兴趣阅读纯文学作品,也可以读法律或教会教条之类的权威文本,二者之间存在区别,必须具有明确的意义,因为它们指导着人们的生活。
只要天主教会能够确定唯一的基督教教义,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宗教改革的兴起,16世纪马丁路德申明由信徒阅读和理解圣经。 路德本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寻求圣灵的帮助获得了正确的指引。 现代解释学理论的定义花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
在17世纪的启蒙时代,理解并不是一个问题。笛卡尔认为思考和条理可以寻得真相。 思考是独立的,语言只用于表达一个人的想法。 逻辑推理寻找与错误推理相对应的“真实意义”,而非“这种感觉的真实性”。 方法论和经验主义是研究的焦点,这一科学分析模型沿用至今。 人们设计了文本分析,语料库研究和程序测试来决定人的理解。
18世纪理想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真理被认为是独有的,语言与思想密切相关,文化决定了人们的思想。 人们对文学和诗歌很感兴趣,因为这里理想主义的特征得到最好的体现。 在目前的跨文化辩论中,我们再次发现了这一点。 翻译被视为一种跨文化的转移,“一种旅程,时空的一个点向另一个点的转移,是旅行者可能在现实中进行的文本旅程”。 将翻译比作装载信息并将其带到海上的船是一种古老的暗喻,但它真的足以描述翻译的作用吗?
4. 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
基于这点,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他将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纳入讨论范围内。他认为在辩论语言时,逻辑推理和个人主义证据都不能保证得出真理。
语言包括两方面,一是客观语法特征和联系文化群体所有元素的文字,二是语言的主观特征,即语言是由人类个体话语创造和发展的。两方面相互依存,仅偶尔清晰地出现。所有作对比研究的语法都仅仅领会了语言一半的真实性。同时个人正确理解的可以由主观的局限性实现,翻译目的论认为功能翻译往往是源语文本主观解释。
真理并非“如此”发现的,既非通过客观的方法论,也非主观的证据,而是与历史有关辩证地获得。任何字词的含义,任何基于文化对事物的理解,任何科学方法都不是绝对的。它们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真理只有在于他人的讨论才可获得,它是共享的。例如一群人在讨论问题,他们可能不久就会得出解决方案,达成观点共识,之后分享真理。如今有个持不同观点的人加入其中,又一轮讨论开始。正因为此,图书馆里才有那么多书。书籍代表着对所谓真理的辩证讨论。
施莱尔马赫认为并不是自发的,它需要辩证地质疑和证明。因此施莱尔马赫意识到制定阐释规则的必要,即“阐释学与批判”。施莱尔马赫为了证实人对文本的理解并解释篇章含义在一个“理解的循环”中建立了几种悖论。即便如此,阐释学仍是一种艺术,这些“理解的准则”没有固定的应用方法,而是根据直觉运用的。
整篇文本与文本中单一元素之间存在理解循环,相互影响,分开理解则会存在偏差。如此,整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我称其为过度汇总质量。
文本结构和文本效果间存在循环。作者在书写时,字里行间可能还藏有别的意思。
主要文本与次要文本特征间存在循环,作者有时需要强调部分内容,如加上副标题,那么译者在做理解翻译时则需注意。
单一文本形式与其他相似文本文体类比间存在循环。透彻的理解可以进行比较,施莱尔马赫已经在200年前列出了后来文本语言学能系统地,有条不紊发展的想法。
但是阐释学绝不仅仅是进行一系列文本分析,这只是开端而已。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根据当时流行的科学模型构思了一种人文学方法论,但是这一方法论过于依赖个体历史了。
5. 阐释学循环
20世纪时,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将哲学话语向新方向带领。他提出了“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并将视角由理解事物转向理解自身。通过语言来表达与理解人类存在的意义。世界好似一个有意义的实体。理解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这取决于个体的现状。绝对纯净的客观理解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理解由个人视角和相关知识水平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第一次听生物化学分析或印度的印度教信仰,抑或南非种族隔离的住房法的讲座,我是听不明白的,因为我没有基础。在我通过接触相关知识,听别人解释后学到一些东西时,我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我对奇怪事实的理解和看法会不同。
这便是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循环”,它不能与施莱尔马赫的“理解循环”混淆。语言学认为真理并不存在与文字表面,而在于文字的含义内,包括自身。这便需要持开放的态度倾听某个观点的含义。
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进一步发展了海德格尔早期哲学中的本体论转向。 伽达默尔说,可理解的存在是用语言构成的。 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交流手段,也能创造意义。 这种语言哲学与所有固有概念相对。 想要理解的人必须按目的发掘文字和人们传达的信息背后的含义。
阐释学聚焦于社会与伦理的内在关系。分析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行为的动机以及对他人的理解,这一点是时刻变化的。有效的历史是有原则的,历史的经验作为一种批判性的人类传统整合吸纳也是文化存在的根基。自由的自主存在是没有的,我们依据语言传统和思维传统生活,他们决定了我们对万物的理解,也创造了可被科学方式证实的真理。
文本作为信息正在增长,通过新颖的相互关系发展其意义。人类的所有主张都有一个动机,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动机。你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后阅读自己的论文或译文时获得这种体验:它们开始让你偏离最初写作或翻译时的想法,同时也能让你学到一些东西。
这一点不是对任何“阐释学真理”的描述,而来自是个人的疑问:我如何理解?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与文本篇章的对话。在阅读时,我们先着重学习,最终达到用阐释学知识理解个人和原文本之间的“界限融化”这一境界。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也明白了篇章的含义。
因此,真理是一中意义的披露,就像经验一样,可作证据使用。阐释学尝试探索个人理解的过程,它并未给出一个模型解释真理的逻辑构成是什么。从这个意义来看,弄清一篇文章的真实含义是永不固定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我们都在不断学习。为了得出这些经验,我们需要对篇章保持开放接受的态度。我的译文是我所理解的文章内容,理解篇章是一种认知现象,译文通过心理表现与原文相连。
文献综述:
阐释学与西方的哲学理论有着内在关系。“阐释学”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意为理解语篇的一种方式。
阐释学在中世纪时用于理解和解释圣经和神谕。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1768-1834)被称为“现代阐释学之父。”他最先将阐释学带入到翻译过程中。他认为阐释学是一门艺术,因为随着历史的变迁、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某些词汇和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表达的理解会不断变化。他认为有两种方式能有效拉近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和读者间的距离:一种是“在不打扰作者的情况下将读者带向作者”,另一种是“在不打扰读者的情况下将作者带向读者。”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是另一位将阐释学带入翻译的学者。他将原阐释学聚焦的对象:“理解与解释”转向“存在的重要性”(R. Stolze, 2002:284)。他认为,完全客观的理解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人的视角和知识储备都决定着他的理解。海德格尔的阐释观认为翻译实践是核心。
乔治. 斯坦纳将阐释学翻译理论推向顶峰, 他是一位出生于法国的美国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他于1975年出版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里,他提出了阐释翻译“四步骤”。他的书被学术界认为是“18世纪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
80年代末期,阐释学被正式引入中国学术圈。著名作家钱钟书(1910-1998)是第一个将阐释学引入中国的学者。在他的书《管锥编》中他提到了一种“阐释的循环。”1987年,阐释学翻译理论开始应用于翻译研究和分析领域。袁锦翔教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期刊上发表了《一种新的翻译文体——阐译》一文,通过比较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9423],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中国古诗词的意象表达与翻译——以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词译著为例开题报告
- 论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豪杰译现象——以《黑奴吁天录》及《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文献综述
-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Tourism Translation开题报告
- “言语”和“静默”外文翻译资料
-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电影翻译的力量外文翻译资料
- 从个人成长视角分析《追风筝的人》中的主角阿米尔的人物性格外文翻译资料
- 个人旅游博客作为研究跨文化交往的文本:来自津巴布韦的美国sojourner博客的试点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接受理论视角下动画电影字幕翻译的比较研究 –以《疯狂动物城》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On DifferenceTranslation Of E-C Plant Metaphors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