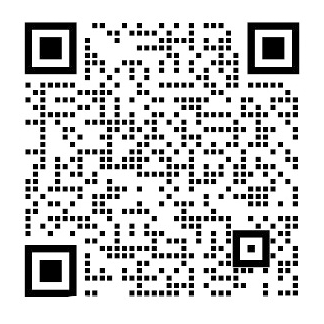文献翻译原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 20141374002 翻译班 王瑞鹏
Extracted from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which is written by Eugene A. Nida. Eugene A. Nida is a well-known American linguist and translator who has proposed the famou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theory. The excerpt is from the 1st page to the 12th page.
节选自尤金·A·奈达的《语言,文化与翻译》,尤金·A·奈达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提出过著名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节选了第1页至第12页的内容。
The 1st page to the 12thpage:
Paradoxes of Translating
Translating is a complex and fascinating task. In fact, I.A.Richards (1953) has claimed that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smos. And yet translating is so natural and easy that children seem to have no difficulty in interpreting for their immigrant parents. These children normally do very well until they have gone to school and have learned about nouns, verbs and adverbs. Then they often seem tongue-tied because they try to match the words and grammar rather than the content.
Because of experience i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n school,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literalness in translating means faithfulness to the text, even though close, literal renderings are often seriously misleading. In English, for example, the repetition of a word usually implies emphasis, but not in Bahasa Indonesia, where repetition only signals plurality. In the Quechua dialect of Bolivia the suffix -rung marks the preceding noun as plural, but in conversation Quechua speakers use the suffix only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ction and do not constantly repeat it,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plural suffix in Spanish. Accordingly, a literal translation which represents every plural -s in Spanish by the Quechua suffix -runa is regarded by Quechua speakers as being not only strange but even an insult to the intelligence of hearers.
Because of the many discrepancies between meanings and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languagesgt; some persons have insisted that translating is impossible, and yet more and more translating is done and done well. Those who insist that translating is impossible are usually concerned with some of the more marginal features of figurative language and complex poetic structures. The use of figurative language is universal, but the precise figures of speech in one language rarely match those in another.
It is true that in some languages one cannot say “My God, “because native speakers insist that no one can 'possess' God, but a person can speak about “the God I worship' or “the God to whom I belong. “Translating is simply doing the impossible well, regardless of the objections of such famous authors as Goethe, Schleiermacher, and Ortega y Gasset who insisted that translating is impossible and yet did not hesitate to have their own writings translated (Guttinger 1963).
Another paradox of translating is reflected in the contention that translating is valid but paraphrase is wrong. In fact, all translating involves differing degrees of paraphrase, since there is no way in which one can successfully translate word for word and structure for structure. In Spanish me.fui is literally lsquo;I went myself, lsquo;in which me is a so-called reflexive pronoun, but this Spanish phrase can often be be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lsquo;I left right away rsquo;or lsquo;I got away quickly.rsquo; In English, as well as in most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one speaks of the lsquo;heartrsquo; as being the center of emotions, but in many languages in West Africa a person lsquo;loves with the liverrsquo; and in som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Central America people talk about lsquo;loving with the stomach. lsquo;Since languages do not differ essentially in what they can say, but in how they say it, paraphrase is inevitabl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semantic legitimacy of the paraphrase.
A further paradox occurs in the widespread view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first produce a more or less literal rendering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n proceed to improve it stylistically. Style, however, is not the frosting on the cake, but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oces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It must be built into the text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t is usually better to aim first at a stylistically satisfactory rendering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n review it carefully to “tighten it up' by analyzing and testing the correspondences. A few errors in the correspondences of lexical meaning are much more excusable than missing the spirit and aesthetic character of the source text.
Since translating is a skill which generally requires considerable practice, most people assume that it can be taught, and to an extent this is true.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really exceptional translators are born, not made. Potential translators must have a high level of aptitude for the creative use of language, or they are not likely to be outstanding in their profession. Perhaps the greatest benefit from instruction in translating is to become aware of onersquo;s own limitations, something which a translator of
Steinbecks Of Mice and Men into Chinese should have learned. Then he would not have translated English mule-skinner into a Chinese phrase meaning lsquo;a person who skins the hide off of mules.rsquo;
For many people the need for human translators seems paradoxical in this age of computers. Since modern computers can be loaded with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why not let computers do the work? Computers can perform certain very simple interlingual tasks, providing there is sufficient pre-editing and post-editing. But neither advertising brochures nor lyric poetry can ever be reduced to the kind of logic required for computer programs. Computer printouts of translations can often be understood, if the persons involved already know what the text is supposed to say. But the results of machine translating are usual1y in an unnatural form of language and sometimes just plain weird. Fur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文献翻译译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 20141374002 翻译班 王瑞鹏
节选自尤金·A·奈达的《语言,文化与翻译》,尤金·A·奈达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提出过著名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节选了第一页至第十二页的内容。
第1页至第12页:
翻译的悖论
翻译是一项复杂而令人着迷的任务。事实上,I.A.Richards(1953)称,它可能是在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然而,翻译是如此的自然和容易,孩子们似乎可以很轻松地为他们的移民父母翻译话语。这些孩子在上学之前,通常可以翻译的很好,但是在学习名词、动词和副词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舌头似乎打了结,因为他们试图去匹配单词和语法,而不是考虑其内容。
因为大多数人有在学校里学习一门语言的经验,他们认为,文字的翻译是要忠实于文本,即使非常接近,字面翻译通常也会严重误导读者。在英语中,一个词重复出现通常意味着强调,但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他们的语言则习惯于重复。在玻利维亚的克丘亚语方言中,-rung为名词的复数后缀,但在交谈中,他们只在开始的时候使用,不会反复重复,就像西班牙语中的复数后缀一样。因此,如果在翻译这两种语言时,如果直译,会被读者认为是一种奇怪且侮辱智商的行为。
由于不同语言的意义和结构的差异,一些人坚持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实际上,翻译工作却做得越来越好 。那些认为翻译不可能的人通常关心的是比喻性语言的一些边缘特征和复杂的诗歌结构。比喻性语言的使用很普遍,但一种语言很难与另一种精确匹配。
在某些语言中,人们不能说“我的上帝”,因为当地人坚持说没有人可以“拥有”上帝,但一个人可以说“我崇拜的上帝”或“我属于上帝”。“翻译只是做不可能的事情,不管是歌德、施莱尔马克和奥尔特加·加塞特·巴布尔这样的著名作家如何反对,他们坚持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也毫不犹豫地会拥有自己的著作译本。(居丁格尔1963)。
翻译的另一个悖论是:翻译是有效的,但意译是错误的。事实上,所有的翻译都有不同程度的意译,因为没有一种方法能成功地将原文逐字逐句地翻译出来。在西班牙中,mefui是我亲自去的意思,在这个词语中,“我”是一个所谓的反身代词,但这个西班牙短语通常可以翻译成英语的“我马上离开”或“我很快就离开。”在英语中,以及其他大多数欧洲语言中,人们说“心”是情感的中心。但在许多语言中,比如在西非,爱与肝脏有关,在一些中美洲的土著语言中,爱与胃有关。虽然语言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说的过程中,意译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意译的语义合理性。
普遍认为,翻译者应该首先对原文进行一定的字面翻译,然后再继续在文体上进行改进。 然而,语言风格不是蛋糕上的糖霜,而是语际沟通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必须从一开始就嵌入到文本中。 通常情况下,首先要对源文本进行风格上的转变,然后通过分析和测试对应关系来将两者融合在一起。词汇含义对应中的错误比起缺少灵魂和审美的源文本而言,更容易被人所理解。
由于翻译是一门需要大量实践的技能,大多数人认为它可以通过教授来学习,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可行的。但是,真正杰出的翻译者是天生的,而非后天培养的。 潜在的译者必须具备高度的才能,才可以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他们的领域中出类拔萃。所以翻译教学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这是斯坦贝克的《老鼠与人》的译者应该懂得的,然后他就不会把英国的mule-skinner翻译成一个中文短语,意思是“剥了驴子皮的人”。
在这个电脑时代,对于许多人来说,对翻译人员的需求似乎很矛盾。 既然现代计算机可以装载字典和语法,为什么不让计算机做这项工作呢? 计算机可以执行某些非常简单的语言任务,只要有足够的预先编辑和后期编辑。但即便是广告小册子和抒情诗,计算机程序都没办法处理。
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原文的内容,那么计算机给出的译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机器翻译的结果通常是一种不自然的语言形式,有时候甚至很怪异。此外,真正的改进不仅仅是修改程序或者增加规则。因为人的大脑不仅具有数字和模拟功能,它也有一个内置的价值系统,这使得它与机器相比,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人总是会对任何文本的翻译文体的引人入胜、语义复杂,包括大多数值得在另一种语言交流是必要的。对于任何一种风格独特,语义复杂的文本而言,人类译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最难翻译的文本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那些不含实际意义的文本,即政治家和代表们经常用于国际论坛的语言类型。实际上,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些专业翻译人员坚持认为,最难翻译的文本是演说者或作家试图什么实际内容都不讲的文本。 其次,难翻译的文本类型是充满了讽刺的文本,因为在书面文本中,语言的深层含义更难被翻译出来。第三种难处理的文本是一本关于翻译的书或文章,其中的例证很少能与之匹配。事实上,一本关于翻译的书几乎需要进行大量的改编。
翻译中最令人诧异的矛盾之一是,从没有一个完美的翻译。因为语言和文化总是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此外,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重叠的意义和模糊的界限,这是逻辑学家的痛处,但却是诗人的喜悦。语言的不确定性是拥有创造力的代价,同时也是对人类经验的象征性重新进行阐释的代价。
有些人认为翻译中最大的问题是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正确对应的词汇和结构。相反,译者最困难的任务是完全理解被译文本的指定意义和联想意义。这不仅涉及了到解单词的意义和句法关系,而且还涉及到了文体手段中的所有细微差别。正如一个痛苦的翻译者总结出的问题,“如果我真正理解了文本的含义,我可以很容易地翻译它。”
也许最不容易理解的翻译矛盾是:一个熟悉两种语言的人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首先,了解两种语言是不够的。了解各自的文化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这本书《语言,文化和翻译》的标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们可以完美地讲两种语言,但是很难写得好,这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熟练的翻译人员。而且,仅仅能够说两种语言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成为一流的口译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除了掌握一门语言之外,口译员还必须能够快速组织语言。莫斯科莫里斯托雷斯研究所对潜在口译员的测试中涉及一个指定的主题,即一分钟准备一个关于该主题的简短演讲。
最难理解的语言悖论是语言的视差,即语言不仅代表现实,而且会歪曲了事实。 例如,当人们充分了解太阳实际上没有在升起或落下,仅仅是因为地球自转时,会使用日落和日出这两个词。同样,人们称某些大耳海豹为海狮,虽然它们根本不是狮子。即使一个词被错误地理解了,许多人也还是倾向于相信它。例如,人们仍然引用谚语来证明规则是作为证明例外的手段,但证明只应在“测试”的意义上去理解。
有些人认为语言是现实的图片或地图,他们很少可以花时间认识到图片和地图不可避免地会失真。图片和地图都有视差,但人们通常习惯于现实的偏斜,甚至会有特殊的装置来计算地球表面的地图和照片中的误差。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忽略语言中的视差,他们觉得口头表述是绝对的真理。他们谈论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它不神圣或不是罗马帝国。最近有学者从西方民主国家的观点来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被普遍接受术语的含义既不民主也不共和国。有些人不再说协议被破坏;他们只是使用“无效”这个词。军队也不再说撤退;他们只是说重组。同样,股市不再下跌,而只是在巩固。
翻译的矛盾基本上是语言和文化的矛盾。 因此,本书的介绍方式是首先解释一些语言的重要特征(第2-6章),然后是讲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即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翻译(第7章)。 第8章涉及功能对等的问题,第9章涉及翻译程序。 第10章讨论各种翻译理论及其与跨语言交际中的关系。
这本书讲的不是关于如何将主动句变成被动句,如何在前景或背景下使用短语,或如何在书面对话中标记反语,因为有很多处理这些问题的书。本书旨在更广泛地理解语言和社会结构中所强调的语际交际问题。因此,翻译处理的主要重点是语言之间的功能对等,作为现实视差的语言不确定性,以及翻译作为一种交流功能而不是一种匹配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特征的系统。作为处理这些问题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很多人谈到了话语特征(包括修辞和风格)以及作为一种类型的游戏的语言功能,这种功能包括关于语言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适用于口头交流的游戏理论中,只有赢家且从没有一个完美的游戏。
语言的功能与理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语际交际中所涉及的内容,必须首先了解语言的主要功能和理论。通过考虑语言的不同功能,可以更好地理解口头交流的惊人复杂性,并且简要了解一下有关语言的重要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是如何交流的。
语言的功能有两种基本类型:心理学类型和社会学类型。 心理功能可以被描述为人们与现实进行谈判的手段,而社会学功能可以说是人与人谈判的方式。心理功能可以基本上认为是内在的或主观的,而社会学功能可以被看作是外部的和人际的。
语言的心理学功能
语言的主要心理学功能是命名,陈述,现实,表达和认知。对一种经验进行命名的心理需求很有必要,因为人们在阅读海伦凯勒激动人心的故事以及她对水的符号给出的强大见解时,并未意识到命名的重要性。大多数小孩对新单词的渴望也突出了用符号来识别和控制事物的重要性。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命名一个人的经历中的某个对象或事件的话,似乎就能够控制这些事件。
但只有命名是不够的。人们想说一些他们命名的物体和事件。 因此,他们会使用主语谓语或主题评论语句,例如“约翰跑掉了”和“我不喜欢他。” 人们还希望能够将这些陈述的字符串连接在一起,因为单个名称太局限,难以满足某些心理需求。
然而,人们需要语言中更深刻的东西,而不是将句子串在一起或命名现象的能力。他们本能地认为,语言可以提供一种观察世界的系统。 如果他们可以叫拉西是一条狗,并且如果所有的狗都可以称为犬类,并且如果所有的犬类都可以称为动物,那么一定有一种方式可以使口头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现实,虽然可能不完美。当人们知道猫这个词不仅可以代表一只宠物猫,而且可以用于谈论狮子,老虎和豹子时,他们发现确实有一个词可以在名称层次结构中具有多种功能,也就是说,它可能有不止一个含义。这类词汇从来都不是对现实的完美反映,但只有一种方式让人们有了概念化的体验。这只是“他们的现实”。
语言的另一个心理功能是表达。这可能会以几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并且不会影响其他人。相反,它的目的是发泄一个人自己的感受。 这种表达可能只是对某些事件的情绪反应的简单例子,例如,“哎呀”,“该死的”,“耶”,还有“哦,天哪”,或者是玩文字游戏,这是小孩喜欢做的事情,也是大人们会常常做的。
然而,表达性语言可能是一种美学上的努力,用来编排文字以达成平衡,比例和对称性。文字也可以被操纵以创造或反映特定的心理氛围,例如,严肃或顽皮,清晰或神秘,必要或暗示。美学表达也可能涉及节奏,无论是语音还是语义。表达性语言的某些美学方面也可能在语言的社会学功能中被利用,因为它们可能对于增加话语的影响或吸引力很重要。但语言的表达能力表达了一个更基本的心理功能。
语言的最重要的心理功能可能是认知,用语言去思考。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认知都是口头的。人们可以根据图形关系或相关的一系列事件来思考,但是所有复杂或抽象的思维都至少会使用某种语言。普通人在认知中使用语言(默默地与自己说话)所花费的时间比除了睡觉之外的任何其他活动(有些人在睡梦中说话)占用的时间更长。大脑内的口头符号不仅占用更多时间,而且就最终目标和益处而言,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
语言的社会功能
语言的主要社会学功能,即人们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这些功能具有以下几种类型:人际交往,信息交流,祈使,表达和情感。 人际功能首先是由于其战略重要性而列出的,尽管在讨论日常情况时,普通人使用语言的方式中会经常忽略它。
语言的人际功能主要涉及人们谈判或维持社会地位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如何利用语言帮助建立自己的社会等级,以及他们如何与其他人保持这种关系。在大多数语言中都有相当不同的层级,包括仪式,正式,非正式,休闲和亲密的演讲。例如,在精心安排的宴会上,一位管家可能会邀请客人进入餐厅,她说:客人现在可以前往宴会厅。 然而,在自己的家中,主人更可能对尊贵的客人说,“我建议我们在餐桌上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在一个亲密朋友的聚会中,一个人可能会说,“来吧!我们吃饭吧”,在野餐会上,相应的表达可能是“来吧,吃吧!”,对自己家庭的成员来说,可能会使用诸如“吃吧”之类的表达方式。
这些不同层次或语言的使用主要以权力和团结为目的。那些希望象征自己权力的人经常会贬低他人,而那些想要增强权力的人往往会模仿当权者的讲话。为了更好地与其他人团结一致,演讲者或作家通常会试图与观众的欣赏水平保持一致。这意味着人们在语言上被分类为“组内”或“组外”。在小组中,无论是专业的还是社会的,小组成员往往会衍生出他们自己的行话和独特的俚语,而这些社交方言可能变得非常独特,以致人们需要说两种不同形式的语言,就像黑人英语和标准美式英语一样。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4450],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中国古诗词的意象表达与翻译——以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词译著为例开题报告
- 论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豪杰译现象——以《黑奴吁天录》及《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文献综述
-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Tourism Translation开题报告
- “言语”和“静默”外文翻译资料
-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电影翻译的力量外文翻译资料
- 从个人成长视角分析《追风筝的人》中的主角阿米尔的人物性格外文翻译资料
- 个人旅游博客作为研究跨文化交往的文本:来自津巴布韦的美国sojourner博客的试点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接受理论视角下动画电影字幕翻译的比较研究 –以《疯狂动物城》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On DifferenceTranslation Of E-C Plant Metaphors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