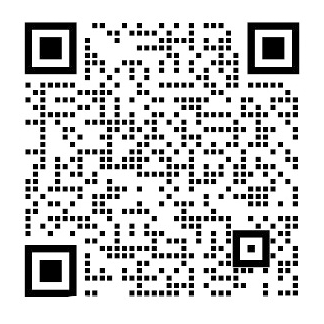文献翻译
出处:Fairclough, Norma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New York:Longman, 1995. 130-138
原文: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first, to set out my own view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second, to illustrate the practic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paper, Towards a Social Theory of Discourse, is a condensed theoretical accou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econd sec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sets out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iscursive events. Readers will find the view of the field sketched out in these sections more fully elaborated in Fairclough (1989, 1992a). The third section makes a transition between the rather abstract account of the first two sections and the illustrative example: it is a reflection on language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ontemporary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it is claimed make a critic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entation to language and discourse socially and morally imperative. The fourth section is a text-based examination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as a process which is pervasively transforming public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igher educ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valu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method to be used alongside others in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on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as a resource in struggles against exploitation and domination.
Towards a Social Theory of Discourse
Recent social theory has produced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nature of language and its function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which have not so far been extensively taken on board in language studies (and certainly not in mainstream linguistics). Social theorists themselves have generally articulated such insights abstractly, without analysis of specific language texts. What is needed is a synthesis between these insights and text-analytical traditions within language studies. The approach developed in this section of the paper is aiming in that direction.
Discourse is a category used by both social theorists and analysts (e.g:Foucault, 1972; Fraser, 1989) and linguists (e.g. Stubbs, 1983; van Dijk, 1987). Like many linguists, I shall use discourse to refer primarily to spoken or written language use, though I would also wish to extend it to include semiotic practice in other semiotic modalities such as photography and non-verbal (e.g. gestural) communication. But in referring to language use as discourse, I am signalling a wish to investigate it in a social-theoretically informed way, as a form of social practice.
Viewing language use as social practice implies, first, that it is a mode of action (Austin, 1962; Levinson, 1983) and, secondly, that it is always a socially and historically situated mode of action, in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facets of the social (its social context) it is socially shaped, but it is also socially shaping, or constitutive. It is vital tha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plor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sides of language use, the socially shaped and socially constitutive, rather than opting one-sidedly for a structuralist (as, for example, Pecheux (1982) did) or actionalist (as, for example, pragmatics tends to do) position. Language use is always simultaneously constitutive of (i) social identities, (ii) social relations and (iii) systems of knowledge and belief - though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salience in different cases. We therefore need a theory of language, such as Hallidays (1978, 1985), which stresses its multifunctionality, which sees any text (in the sense of note 1) as simultaneously enacting what Halliday calls the ideational, interpersonal and textual functions of language. Language use is, moreover, constitutive in both conventional, socially reproducshy;tive ways, and creative, socially transformative ways, with the emphasis upon the one or the other in particular cases depending upon their social circumstances (e.g. whether they are generated within, broadly, stable and rigid, or flexible and open, power relations).
If language use is socially shaped, it is not shaped in monolithic or mechanical ways. On the one hand, societies and particular institutions and domains within them sustain a variety of coexisting, contrasting and often competing discursive practices (discourses, in the terminology of many social analy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ular discursive events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language use) and underlying conventions or norms of language use. Language may on occasion be used appropriately, with a straightshy;forward application of and adherence to conventions, but it is not always or even generally so used as theories of appropriateness would suggest (see paper 10 for a critique of such theories).
It is important to conceptualize conventions which underlie discursive events in terms of orders of discourse (Fairclough, 1989, 1992a), what French discourse analysts call interdiscourse (pecheux, 1982; Maingueneau, 1987). One reason for this is precisely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ursive event and convention, where discursive events commonly combine two or more conventional types of discourse (for instance, chat on television is part conversation and part performance: Tolson, 1991), and where texts are routinely heterogeneous in their forms and meanings. The order of discourse of some social domain is the totality of its discursive practic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complementarity, inclusion/exclusion,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for instance in schools,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the classroom,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文献翻译
出处:Fairclough, Norma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New York:Longman, 1995. 130-138
译文:
本文的目的首先是阐明我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观点,其次是通过讨论当代英国公共话语市场化来说明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本文的第一部分“迈向社会话语理论”是批评话语分析的浓缩理论说明。第二部分“分析框架”为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三维框架。读者将会发现在费尔克劳夫的作品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些部分所概述的观点。第三部分把前两部分中相当抽象的叙述与说明性的例子之间进行了转换:它是当代(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和话语实践的反映,它表明对社会和道德上的语言和话语做出批判的社会和历史取向是必要的。第四部分是基于文本对话语实践市场化的考察,这是一个正在普遍改变当代英国公共话语的过程,尤其是高等教育。本文最后讨论了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与其他方式一起用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并作为反对剥削和统治斗争的方法的价值。
迈向社会话语理论
最近的社会理论已经对语言的社会性质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提出了重要见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语言研究(当然不是主流语言学)中被广泛接受。社会理论家自己已经抽象地阐述了这些见解,但还没有分析具体的语言文本。现在所需要的是这些见解和语言研究中的文本分析传统之间的综合。本文的这一部分提出的方法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话语”是社会理论家和分析家(例如:福柯,1972;弗雷泽,1989)和语言学家(例如斯塔布斯,1983;范戴克,1987)所使用的一个类别。像许多语言学家一样,我会将话语主要用于口语或书面语言,尽管我也希望把它扩展到包括其他符号学模式的符号学实践,例如摄影和非语言(如手势)交流。但是,在将语言用作话语时,我希望以社会理论上可靠的方式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进行调查。
按照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看待语言使用意味着它首先是一种行为模式(奥斯丁,1962; 莱文森,1983);其次,它始终是一种社会和历史上的行为模式,与社会(它的“社会背景”)的其他方面具有辩证关系。它是社会形态,但它也是社会塑造的,或者是构成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必须探讨语言使用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组成性这两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不是片面地选择“结构主义者”(例如,派彻(1982))或“行动主义者” (例如,语用学倾向于这样做)的位置。语言使用总是由这些条件同时构成:(1)社会身份,(2)社会关系和(3)知识和信仰体系——尽管在不同情况下程度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语言理论,比如韩礼德的理论(1978,1985),它强调它的多功能性,它把任何文本(在注释1的意义上)看作是同时具有韩礼德所说的语言的“观念”,“人际”和“文本”功能。此外,语言使用在传统的社会再生方式和创造性的社会变革方式中都是基本的,强调特定情况下的一种或另一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环境(例如,它们在广义上是稳定和严格的,还是灵活和开放的权力关系)。
如果说语言使用是社会形态的,它不是以单一的或机械的方式塑造的。一方面,社会及其内部的特定机构和领域支持各种共存,对比和经常相互竞争的话语实践(许多社会分析家的术语中的“话语”)。另一方面,特定的话语事件(语言使用的特定“实例”)与语言使用的基本约定或规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语言有时可以通过直接应用和遵守惯例被“适当地”使用,但它并不总是或者通常如适用性理论所暗示的那样被使用(见第10章对这些理论的批评)。
根据话语秩序(费尔克劳夫,1989,1992a),将构成话语秩序的惯例概念化是非常重要的,法国话语分析家称之为“话语间性”(派彻,1982; 曼戈诺,1987)。其中一个原因正是话语事件和惯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话语事件通常结合了两种或更多种传统类型的话语(例如,电视上的“聊天”是部分对话和部分表演:托尔森,1991),并且文本在形式和含义上通常是不同的。某些社会领域的话语秩序是其话语实践的整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互补,包容/排斥,反对)——例如在学校中,课堂话语实践,评估书面作品,操场和工作室。而社会的话语秩序则是这些更多的“地方”话语秩序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学校话语秩序与家庭或社区话语秩序之间的关系)。话语秩序之间的边界和隔离可能是冲突点和争论点(伯恩斯坦,1990),作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和斗争的一部分(教室与家庭或社区之间的边界将是一个例子),可能会被削弱或加强。话语实践类型的分类——话语秩序的要素——是困难的和有争议的:为了目前的目的,我将简单地区分话语(话语作为计数名词),代表特定角度的经验领域的方式(例如父权制与女权主义话语)以及种类,与特定的社会批准的活动类型相关的语言的使用,例如求职面试或科学论文(另见Kress,1988,关于话语和体裁的区分)。
我所说的批评话语分析是指系统地探讨(1)话语实践,事件和文本与(2)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关系和过程之间不透明的因果关系和决定的话语分析;调查这种做法,事件和文本是如何由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在思想上形成的,并探讨话语与社会之间这些关系的不透明性本身如何成为确保权力和霸权的因素(见下文)。在提到不透明性时,我认为话语权,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这种联系对于那些参与者来说可能是不清楚的,更普遍的是我们的社会实践与看似并不明显的原因和影响紧密相关(布尔迪厄,1977年)。
分析框架
我使用三维分析框架来探索特定话语事件中的这种联系(见论文5)。每个话语事件都有三个方面或多个方面:它是一种口头或书面语言文本,它是涉及文本生成和解释的话语实践的一个实例,它是一种社会实践。这是三个可以采取的观点,三种互补的阅读方式,一个复杂的社交活动。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分析中,我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关于权力与统治关系中的话语事件。我的分析框架的一个特点是,它试图将基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权力理论与基于互文性概念的语篇实践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互斥理论——见下文)结合起来。文本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被看作是由话语实践调节的:一方面,文本生成和解释的过程由社会实践的性质塑造(并帮助塑造),另一方面生产过程塑造文本(并在文本中留下“痕迹”),解释过程根据文本中的lsquo;提示rsquo;进行操作。
文本的分析是形式与意义分析——我以这种方式定义它来强调它们之间必要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任何文本都可以被看作是交织“观念”,“人际”和“文本”的意思。他们的领域分别是世界和经验的表现和意义,参与者身份的构成(建立,复制,谈判)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和个人关系,以及给定的新的前景与背景信息的分布(在最广泛的意义)。我发现区分人际功能的两个子功能是有帮助的:“身份”功能——个人和社会身份构成中的文本和关系功能——关系构成中的文本。对文本中这些交织意义的分析必然归结为对文本形式的分析,包括它们的通用形式(例如叙述的总体结构),对话组织(用术语,例如,话轮转换),句子之间的衔接关系以及复杂句子中的关系,句子的语法(包括传递性,情绪和形式问题)以及词汇。大多数以语用分析为名的词(如分析发言的力量)都在文本和话语实践之间的边界上。(有关更详细的分析框架,请参阅费尔克劳夫(费尔克劳夫,1992a),下面将举例说明。)
话语实践分析涉及社会认知(费尔克劳夫(1989)和论文1)文本生成和解释方面,而不是社会制度方面(下面会讨论)。分析涉及到对参与者如何产生和解释文本的详细的瞬时解释,对话分析和语用学研究,关于话语事件与话语秩序关系的分析,以及关于哪些话语实践以何种组合正在被吸引。我的主要兴趣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后者。话语间性的概念凸显了由不同类型和话语组合构成的文本的不均一性。话语间性的概念模仿互文性(克里斯蒂娃,1980),与互文性紧密相关,它像互文性一样突出文本的历史观点,转化过去——目前的惯例或先前的文本——转化为现在。
话语事件作为社会实践的分析可能涉及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情境背景,制度背景,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或文化背景(马力诺夫斯基,1923; 韩礼德和哈桑,1985)。关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关于意识形态,参见汤普森(1990))可能出现在三个层面中的每一个层面上。如论文5所示,我认为从霸权角度考虑话语权力是有用的(葛兰西,1971; 费尔克劳夫,1992a)。在互动性的概念——流派和话语的无休止的组合和重组中,看似无限的话语实践中创造力的可能性实际上受到霸权关系和霸权斗争状态的限制和约束。例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霸权,创造的可能性可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20世纪50年代规范实践对跨性别互动的支配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权主义男性霸权争论相关的话语实践的创造性爆发之间形成了相当大的对比。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与话语
批判性话语分析在许多语言学部门中被倾向于视为语言研究边缘的(并且在很多方面是可疑的)领域。在我看来,它应该处于重构的语言学的中心,最近克雷斯(1992)呼吁适当的社会语言理论。我在这一部分的第一个目标是表明对这种来自对当代社会语言和话语(即lsquo;话语秩序rsquo;)的“状态”的分析立场的有力支持:如果语言研究要与当代语言使用的现实联系起来,就必须有社会的,批判的和历史的倾向。第二个目标是为下一节讨论的公共话语市场化过程填补更广泛的背景。
这一部分的前提是,话语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历史常数而是一个历史变量,所以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话语社会功能存在质的差异。还有其不可避免的连续性:我认为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之间不存在激进的分裂,而是在文化主导方面的质变(威廉姆斯,1981),即在特定时代具有最显著影响的话语实践的性质。我将在下面特别提到英国,但全球话语秩序正在出现,许多特征和变化具有准国际性质。
福柯(1979年)对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权力本质和功能的质变的研究,暗示了现代社会中一些话语和语言的显著特征。福柯已经展示了现代生物能源是如何依赖于社会机构(例如学校或监狱)的日常实践中包含的权力和技术,并且是社会主体的产物。例如,“检查”技术并不完全是语言学的,但它基本上是由话语实践,类型,例如医疗咨询/检查和其他各种采访(费尔克劳夫,1992a)所定义的。一些关键的体制类型,比如面试,还有最近的咨询,都是现代社会话语秩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前现代社会相反,现代话语的特点是在权力关系和社会身份的构成和再生产中具有独特的而且更重要的作用。
这种现代性的福柯式权力解释也意味着20世纪社会理论对意识形态的重视,将意识形态作为权力与统治的社会关系得以维持的关键手段(格拉姆西,1971;阿尔都塞,1971;霍尔,1982),作为权力关系连续性和再生产习俗的常识常态化的基础。而哈贝马斯(哈贝马斯,1984)通过他对经济和国家对生活世界的逐渐殖民化的假设,对“现代性”话语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转折点,这意味着“战略”实践取代“对话”实践,它体现了纯粹的有用的(现代)理性。例如,广告和宣传话语已经在当代社会拓殖了许多新的生活领域(详见下文和下一部分),这一过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不应该省略语言标准化这一现代性现象的语言和话语的简要回顾,这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就是通过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强加标准语言来统一语言秩序和“语言市场”(布尔迪厄,1991)。现代社会的许多这些特征在当代“后资本主义”(曼德尔,1978)社会中仍然显而易见,但是也存在影响当代话语秩序的某些重大变化;因此它们表现出现代主义和一些评论家(詹姆士,1984;拉什,1990)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混合。在其他话语领域,“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认同是困难的并且有争议的。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非常有选择性地将当代文化的两个最新论述作为“后现代性”(参见吉登斯(1991))以及贝克(1992)关于lsquo;风险社会rsquo;的相关讨论和lsquo;促销文化rsquo;(参见韦尼克(1991)和费瑟斯通(1991)关于lsquo;消费文化rsquo;),暂且确定当代话语实践中三组相互关联的发展。
当代社会是“后传统社会”(吉登斯,1991)。这意味着传统不得不被证明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公共关系正在下降,例如基于亲属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的个人关系;还有人们的自我认同,并不是作为特定职位和角色的特征,而是通过谈判过程反思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关系和身份需要通过对话进行谈判,这种开放社会比传统社会的固定关系和身份带来更大的可能性,但也带来更大的风险。谈判关系日益增加的结果是,当代社会生活需要高度发达的对话能力。在工作中,作为服务业扩张和转型的一部分,“情感劳动力”(霍赫希尔德,1983)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交际劳动力也在增加。在专业人士和公众(“客户”)之间以及与伙伴,亲属和朋友的关系中也是如此。这些要求可能是困难的主要来源,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轻松满足他们;在语言教育面对面和群体互动的“交际技能”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焦点。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可以理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其特定话语方面发生的“非正式化”过程(沃特斯,1986; 费瑟斯通,1991),我称之为公共话语的“对话化”(费尔克劳夫,1992a,1994和论文5)。对话化是当代话语秩序的一个普遍的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实践对公有领域的殖民化,一种对我们都可以达成的话语实践开放,而不是传统的实践精华和独特的传统实践公共领域,因此是一个更开放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是公有领域对私人领域做法的侵占:在上述暗示的谈判关系和身份的复杂过程中,需要在后传统公共场合注入实践。会话化的矛盾性更进一步突出:它常与话语中的宣传目标的“综合个性化”,以及话语的“技术化”相关。
系统地运用社会生活知识来组织和转化反思性,是当代社会(吉登斯)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其独特的当代形式中,反思与吉登斯所谓的专家系统有关:由专家(如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457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中国古诗词的意象表达与翻译——以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词译著为例开题报告
- 论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豪杰译现象——以《黑奴吁天录》及《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文献综述
-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Tourism Translation开题报告
- “言语”和“静默”外文翻译资料
-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电影翻译的力量外文翻译资料
- 从个人成长视角分析《追风筝的人》中的主角阿米尔的人物性格外文翻译资料
- 个人旅游博客作为研究跨文化交往的文本:来自津巴布韦的美国sojourner博客的试点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接受理论视角下动画电影字幕翻译的比较研究 –以《疯狂动物城》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On DifferenceTranslation Of E-C Plant Metaphors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