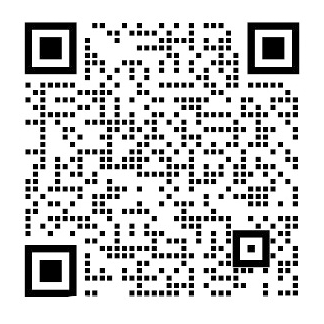Translation,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s
Since the 1990s,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much debated topic — mostly in USAmerican scholarship and/or published in English — and this is perhaps related to an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fields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humanities (see, e.g., Damrosch; Dhaen; Dhaen, Damrosch, Kadir; Dhaen, Domiacute;nguez, Thomsen; Kadir; Lawall; Pizer; Sturm-Trigonakis; Thomsen; Touml;touml;sy de Zepetnek and Mukherjee). In Chinese scholarship, 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 is also relevant whereby emphasis falls on making Chinese literature more visible within other culture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related to the issue of turn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part of world literatures.
All literature is intrinsically national: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literary works are written first in a given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refore nationality of this language determines the nationality of its literature, but also because a language conveys ideas, values, emotion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which are determined culturally. However, not all literary works written in a national language become part of a national literary canon and some works are eliminated, while others come to form part of the canon and are regarded as classic models of the particular national literature. Some works which are popular and a classic model in a certain period may no longer be so in another period. Thus the creation, sele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production, reception, distribution, and (re)reading of texts constitute a complex process whereby it operate by means of multidimensional selection mechanisms involving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n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entities (see Li and Guo). If Chinese literature wants to be read abroad and in other cultural surroundings, it needs to be understood and recogniz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while still remain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s own intrinsic value and valuation. This means that it must 'travel' to other national literatures by means of translation including not only by the conversion of language, but also by cultural variations so that 'the principles of selection never being un-correlatable with the home co-systems of the target literature' (Even-Zohar 241).
Personal choice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 interests. For example, in 1947 Ditch diplomat serving in the U.S. Robert Hans van Gulik translated the Chinese novel狄公案 (Judge Dee) in his spare time claiming to have translated it as a way to practice his English and because he found the story more interesting than texts he has read recently (see Barkman and Vries). Community choices are related to ideological tendencies and serve the purposes of a given community. For exampl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carried out by the Jesuits had more to do with their missionary work as Matteo Ricci admitted when referring to his translations and said that it was don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European scholars, but to 'use it as the tool to convert Chinese to Christianity' (see Ma and Ren 34; unless indicated otherwise, all translations are ours). Further, national interests emerge at times when the entire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situation is at a turning point either because national communities experience some kind of cultural crisis or literary vacuum or because other national literatures contribute to the stimulation of literary developments. This may be the case today, but a similar situation occurred in the period known in China as the May 4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when large numbers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order to revitalize Chinese literature (see, e.g., Zheng).Revitalization is bound to influence in the following sense of processes: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that consists chiefly of a canon, a body of works and their presence as models of literary quality in the minds of scholars and writers. But the phrase 'world literature' is not used exclusively in so normative a sense. Another sens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recent years, makes 'world literature' be an equivalent of global literary history, a history of relations and influences that far exceeds the national canons into which academic departments routinely squeeze and package literatu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academic departments nationalize literature: departments are an invention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versity, a supranational medieval institution re-chartered by the monoglot nations of the industrial era.) An obvious improvement on the anachronism and petty chauvinism of national canons, this global literary history remains under-valued so long as it leaves untouched by analysis the rival accounts of global history that occupy economists, historians and geographers. (Saussy 291)
Thus world literature needs to happen — as it were — along the following lines: 'Setting up a comparative transcultural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at would present its own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and fallacies but would simultaneously offer an effective and understandable assessment of the topic at hand (literary influence, period styles, revolutionary trends, global currents and convergencies, etc.), and thereby would reconcile the dangerous and cautionary aspects of theory with the need to maintain a disciplinary endeavor (the writing of a literary history, no matter how it is defined, be it in national, comparative, or global terms) presents a task that is both daunting and fraught with pitfalls' (Sucur 95). Al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choices — personal, communal, national — which motivate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there are two seemingly opposite situations: in the first the translator selects texts similar to his/her own culture and whic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翻译、跨文化解释和世界文学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的概念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主要是在美国学术界或英语出版物中----这也许与人文学科内学科和领域的融合有关。在中国学术界中,由于中国文学在其他文化中的显要地位,世界文学的理念也十分重要,而中国文学的国际化则与民族文学转向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有关。
所有的文学本质上都是民族的:这不仅是因为文学作品是以一种特定的民族语言书写的,因此这种语言的民族性决定着它的文学的民族性,而且因为一种语言传达了文化上所确定的思想、价值观、情感和许多其他方面。然而,并非所有以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都会成为民族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一些作品消失了,而另一些作品则成为了经典的一部分,成为了特定民族文学的经典模式。在某段时间流行的一些经典作品在另一时间可能不再流行。因此,国家文学的创造、选择和流通与文字的产生、接受、传播和 (重新)阅读的历史背景有关,这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通过个人、社区、国家和跨国实体的多层面选择机制运作。如果中国文学要在国外和在其他文化环境中拥有读者,它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中易于理解和辨识,同时仍然保留自己的内在价值和评估体系。这意味着它必须通过翻译'跨越'到其他国家的文献,不仅包括语言的转换,而且还包括文化的转换,从而使'选择原理与目标文献的并存系统不相关'(佐哈尔241)。
个人选择通常与个人利益有关。例如,1947年,美国外交官罗伯特 · 汉斯 · 范 · 古里克在业余时间翻译了中国小说《狄公案》,声称将翻译作为一种练习英语的方式,因为他发现这个故事比他最近读过的文章还有趣 (见巴尔卡曼和弗里斯)。社区选择与意识形态倾向有关并且服务于特定社区。例如,耶稣会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上花的功夫,比他们的传教工作更多,因为马特奥 · 里奇在谈到他的翻译时说,这不是为了给欧洲学者带去中国智慧,而是“用它作为将汉语转换为基督教义的工具”(见 MA 和 REN34;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皆为自行翻译)。此外,国家利益有时出现在整个国家或是跨国业务状况处于转折点的时候,比如各国在经历某种文化危机或文学真空,或者他国文化刺激了本国的文学发展。这可能发生在此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五月四日的新文学运动发起之时,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以振兴中国文学(见,如Zheng)。文化复兴必定会受到以下过程的影响:
世界文学的概念主要由标准、作品主体以及它们在学者和作家心目中作为文学典型的认为组成。但是,“世界文学”这个词并不是十分规范地使用。另一方面,近年来“世界文学”地位的日益凸显,使其等同于全球文学史,对于关系和影响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学术部日常压缩和包装文学的国家标准。(意料之中的是,学术部将文学国有化:部门是十九世纪大学的发明,这是一个中世纪的超国家机构,由工业时代使用单一语言的国家重新建立。)虽然这个全球文学史对时代主义和小沙文主义有了明显改进,但只要它没有经过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全球历史对立面的分析,就仍然受到低估。(291)
因此,世界文学需要像曾经一样沿着这样的顺序:“建立一个相对的跨文化的文学历史,呈现自己的理论局限性和谬误,但同时也要对当前的主题进行有效和易于理解的评估(文学影响、时代风格、革命趋势、全球性的流通和汇合等)。因此,努力保持一种跨学科的需求 (关于文学史的写作,无论它是如何定义的,是从国家、相对性还是从全球来看),都将缓解理论上的的危险和警示作用,这是一项既艰巨又充满诱惑的任务”(sucur 95)。众多选择——个人的、社区的、民族的——都会促使在翻译、解释、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两种似乎相反的情况:首先,译者会选择类似于他/她自己文化的文本,因为这样的文本更易于本国读者理解,其次译者会选择不同于他/她自己的本土文化的文本,但是他/她自己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关键。在过去,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是比较容易的。之后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障碍和阻力。然而,在每种情况下,文本都需要通过本国文化的过滤。
与国内文学的选择机制不同,世界文学和翻译文学的选择过程是要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外国文本远不及本国文本的可理解度和感兴趣度。题词开始于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一直是一个精挑细选的、目的明确的过程,并在话语策略发展中得以继续翻译,始终首选本国话语而非其他”(Venuti468)。这意味着翻译中的文本总是失去关于源文本的一些内容,但也获得了一些东西,主要是跨越自己民族文化的界限,并在其他国家被阅读和理解。这也意味着本国文学不会立即进入其他国家的文学领域。只要它被翻译,就会有再写、变异和误读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间转化的问题:世界文学是一个“在翻译过程中形成的······国家间文化的椭圆折射······不是文本既定的标准,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全世界超越时间和地点的分离形式”(Damrosch,什么是281)。所谓的“椭圆折射”不同于简单的反映: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均匀的镜子前面,那么镜子中的图像就是这个人的形象的简单反映,但是如果这个人站在一个不均匀的镜子前面,那么图像就会变成椭圆形的折射。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形成这种椭圆折射而不是简单的反映,由于世界文学与源文学和目标文学有关,这种折射本质上是“双重的”。在源文学和目标文学的交叠双重区中形成了一种椭圆效应:世界文学便形成于这种中间区域,与两方文化有关又不局限于任何一方。
我们认为,在世界文学方面,谈论文化的转化是不够的。不仅要强调特异性和独特性,而且还要强调同一性、共性和文化融合性。不仅需要研究单向变化,而且还需要探究双向和多方向的变化。世界文学是指能够超越特定的民族文化界限的民族文学,并达到其他文化的读者可以阅读和理解的共通的程度,这既体现了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又体现了变化与融合:“一个民族的文学呈现出了所有的问题。它必须说明不同人们的自我论断,即所谓的根基,并且这也是他们如今所追求的。这就是它的神圣作用、史诗或是悲剧。它必须表达——如果它不(并且只有它不),它仍就是垂死的、民俗的区域主义者——一个文化与另一个不同文化的关系着推动整体化的实现。这就是它的分析和政治功能,只有在需要质疑其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时候才可实现”(Glissant 252)。
在西方文学界中,“影响/接受”或“核心与边缘”的典型常常用来解释世界文学中所涉及的过程:“如果西方文学不再需要以严格的正式化的形式存在于世界上,在这些针对西方历史的严重指控之后,那便成了一个不重要的过程,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将被定义为一种平庸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与这个世界之间的新的关系,他们将不再占据同一领域中的卓越地位,而是在多样化中担任共同任务”(GISSant252)。如果我们能说明人们将西方文化中的独特性和特异性视为世界中心的理论,并指明非西方文化中的共性和个性存在于与之相对应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之中,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为世界文学的研究建立一个新的框架。表面上来看,主流文化似乎对较弱的文化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事后看来,这种“中心/边缘”的模式实际上有一个大漏洞(在此,请参见,例如 ,Juvan,http://docs.lib.purdue.edu/clcweb/vol15/iss5/10)。在很大程度上,该模式忽视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多层面性质,它影响了各种形式的知识,但更多的是通过文学传播的知识:一种语言主体不明确,由于个人、社区和国家的差异,产生不同形式的解释。当这种影响进入文学和文化领域时,这在许多情况下是相互的,因此,文化流通的过程是变化的并且是双向变化的。
Lidia H.Liu 重新审视了东西方之间关于欧洲文本翻译成非欧洲语言的主要联系。她指出,翻译应当是改编、转换和其他跨语言实践的简要表达:传统的翻译理论家用来指定翻译中涉及的语言,如 “源语言”和“ 目标语”,这些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还具有误导性······源语言的概念常常依附于真实性、起源、影响等因素,并具有重新将由来已久的可译性/不可译性的问题带到讨论中的缺点。另一方面,目标语这一概念蕴含着严重的目的色彩,需要跨越文化才能获取丰富的意义;因此它歪曲了宿主语言等效性的构思方式,使中介处于第二重要位置”(27)。此外,Liu 建议通过“主语言”和“客语言”来表示翻译文本(目标语言)和原始文本(源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强调非欧洲的主语言可以在翻译过程中由客体语言修改,与它形成融合关系,或者侵占、替换和甚至决定客语言。从跨文化研究和解构的角度来看,这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概念,J.Hills Miller关于语“主”和“客”,介绍了一种类似多维动力学的形式,以进行批判性解释。Liu所指出的传统翻译理论的缺陷也适用于中西文化动态比重再分配的跨文化影响研究。
例如,当谈到世界文学时,西方学者通常会提到歌德的理论,当歌德提出韦尔特文学的概念时,他的灵感来自于1826年出版的《浪漫玉娇梨》,法语版为《 Iu-Kiao-Li ou Les Deux Couines 》(见,例如 Birus,http://dx.doi.org/10.7771/1481-4374.1090;Eckermann)。这表明在歌德看来,中国文学具有普遍价值,并且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将世界文学视为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循环旅行是合理的:'世界文学本身是一个旅程的概念,但它不是从西方到东方,它最原始的时候是东方的,逐渐发展成西方的理论概念,然后又回到东方或整个世界'(王14)。李通过赵氏孤儿来研究这种循环性,从古代中国文化到西方文化,再回到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去。赵氏孤儿的作者是纪君祥(确切生平不详),元代剧作家 (1206-1368),伏尔泰、林兆华(1936-)和他一致认为,'这种环形旅程不再是A 与 B 之间的二维或线性关系,而是三维环形结构,是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 '(90),因此世界文学是跨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明,也是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 (也见 Li 和 Guo)。
在'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高效跨学科关系'中,john pizer 指出达罗奇在2003年发表的《世界文学是什么?》通过翻译和考古学中政治、商业、竞争效应来调节各个时间空间的文学著作来“遵循跨国际循环”中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Dambrosch 认为,如果一个作品能够起到超越本土文化领域的作用,那么它将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认为虽然翻译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些文本的原始意义,但是当它使作品在循环模式下国际化以及应对跨时间的不同文化对跨国、跨网络解释学对话的挑战中,世界文学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提高。 在Damrosch的观点中,关于编辑和翻译这些文本的争论实际上提高了它们作为世界文学的地位,因为这种争议继续激发人们对这些作品的重大兴趣。(11)
Pizer认为Damrosch对世界文学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在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范例(这是与90年代以来进一步发展的Steven Totosy de Zepetnek的'比较文化研究'的框架相同的概念,参见,例如,“从比较的角度分析”lt;http://dx.doi.org/10.7771/1481-4374.1041gt;;另见Totosy de Zepetnek和Vasvari)。Pizer 还表述了世界文学与跨文化口译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的说明。
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在促进本国文学方面会遇到以下三个困难:1)一个不属于任何主要世界语言的语言本身就成为接受力的阻碍,2)由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相对薄弱,一个既定国家的文化可能不会受到全世界的重视,3)具备国家特殊性和独特文化细节的作品可能会给外国读者带来文化理解上的困难。随着对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不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而是一个“新兴市场”:不仅是整个经济和制造业,而且文化产业也在崛起,中国的文化政策包括将这些研究纳入大学课程(见,例如,Wang 和 Liu)。然而,为了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知名度,必须作出更大的跨文化交流方面的努力(我国地域广阔,出现了全国性的巨大变化),因此,各种语言(不仅是汉译英或英译汉)的翻译也增加了。
虽然跨文化口译的现象长期存在,但我们简要介绍了中国的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司马迁(公元前135-86)的史记从公元前2600的黄帝时代到他自己的时代对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这是发现跨文化观念和模式的最早的例子之一。在现代,王的作品“《红楼梦》述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发现了类似于1934年的陈寅恪指出的跨文化口译,即“外国概念和国际资源相辅相成。”关于现代中国文学评论运用西方理论,这只表明是一种误导性的方法(见如陈、鹏祥、另见黄、曹),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在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和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研究中存在局限性,因为它是一个从西方到东方的单向的过程,并不包括中国的思想。从王国维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虽然他没有翻译叔本华的原始作品,但他在中国文化的框架内对叔本华的哲学理论进行了分析、选择和改造。另一个少见的例子是陈艾门和杨立新在2003年,在跨文化语境中收集到的大量比较文献,其中的作品不仅广泛地运用了西方的思想,而且还广泛借鉴了中国的思想。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8134],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中国古诗词的意象表达与翻译——以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词译著为例开题报告
- 论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豪杰译现象——以《黑奴吁天录》及《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文献综述
-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Tourism Translation开题报告
- “言语”和“静默”外文翻译资料
-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电影翻译的力量外文翻译资料
- 从个人成长视角分析《追风筝的人》中的主角阿米尔的人物性格外文翻译资料
- 个人旅游博客作为研究跨文化交往的文本:来自津巴布韦的美国sojourner博客的试点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接受理论视角下动画电影字幕翻译的比较研究 –以《疯狂动物城》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On DifferenceTranslation Of E-C Plant Metaphors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