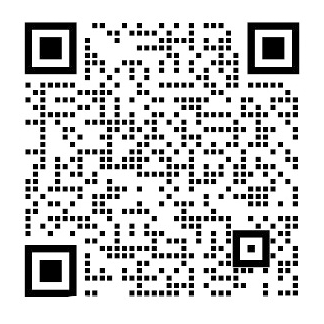外文文献原文
Writing Tibet as Han Chinese sojourners: the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place in an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Junxi Qian,Hong Zhu.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6,182(4):418-428
Abstract
This paper engages with the debates on place, and develops an analysis of a corpus of writings on Tibet produced by Han Chinese writers, documenting their experiences of sojourning in Tibet.Recent literature in human geography has conceptualised place as a centre of meanings.Moreover, it has been recognised that place is implicated in the fashioning of the self.Following these theorisa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Han writers senses of place for Tibet enable them to explore and fashion their identities,and build an alternative lifeworld to the allegedly alienated and rationalised life in the China Proper (neidi).This study puts forward its arguments in tandem with two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On the one hand, it suggests that place is a performance that coheres around constructed discourses and lived practices. Hence, this article analyses both the ways in which the Han writers frame Tibet into a system of discourses and meanings,and how these discourses feed into routinised, lived practices at the level of the everyday life.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how Tibet as place is situated in the tension between local particularity and the wide network of places that constitutes Chinas post-reform transformation.The writers texts play out a sense of place being eroded and on the verge of being ruined.Notably, they negotiate the restless transformation of Tibet in profoundly ambiguous and contradictory ways.
INTRODUCE
This article builds on theories of place to examine the above-mentioned writings on Tibet.It draws on two parall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section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argued that place is not a static given, but a performance that coheres around constructed discourses and lived practices (Bennett 2014).For the Han writers, their lifeworlds in Tibet are mediated by historically specific discourses making claims to the lsquo;intrinsicrsquo; nature of Tibets placeness.
These discourses, in turn, provide a shared frame of values, beliefs and goals (Martin 2003) that shapes the sojourners mundane practices and encounters with Tibetan others. Meanwhile, place, especially in modernity, is innately susceptible to translocal spatialitie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lace
Place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ocial site that is constructed simultaneously by discourses and lived practices (Bennett 2014).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are both ongoing processes, contingent on internal dynamism of place and interactions with outside elements。In this sense, place is never a finished project, but an event and happening (Cresswell 2015).
On the one hand, experiences of place are mediated by truth-claiming, ideologically loaded discourses (Cresswell 2015).Davis (2005) offers a detailed theoris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lace and discourses.。In his view, each group builds up a specific conceptualisation of a given place, by drawing meanings from certain attributes of that place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Representations of place are never purely objective, but reflect what people are predisposed to look for.
On the other hand, place is also lived and practised, through actual encounters with materiality, culture, people and social relations which weave together its fabric.Malpas (1999) contends that experience of place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simply as a subjective, emotional response to objective attributes of place.Instead,lsquo;place is integral to the very structure and possibility of experiencersquo;(Malpas 1999, 32).Place presents itself as a habitus – the schematising of materi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 in which actions embed themselves (Casey 2001)or, to use Martins(2003) term, a framework that sets the perimeters of place-based activities.。Also, place as a structured habitus is lsquo;something we continually put into action rsquo;(Casey 2001, 687, original italics)——it is acted upon and constantly actualised by lived practices and actions. Resonating with these theorisations,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it is at the level of the everyday that we make sense of place through emergent and conflicting experiences(Bendiner-Viani 2013).In sum, the fecundity of place-based practices results in a structure of feeling that involves affective resonances and belonging.It, in turn, acts as a frame within which future activities and practices can be realised and enacted (Duff 2010)
Relational place and the making of space
In the meantime, the potential lsquo;erosionrsquo; of place by wider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captures much of our cultural sensibility(Escobar 2001; Castree 2004).In mundane lives,this tension is often experienced a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bulous ideas of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which lead to homogenisation and abstractness, and the lived realities of place,which, for many, embody the natural, inclusive ways of life and authentic cultures(Davis 2005).Yet, place can never be utterly attenuated. Instead, it undergoes ongoing negotiation and definition (Taylor 1999).Modernity does not impose a seamless and abstract order, but rather creates ambiguity, contradiction and struggle.Exogenous forces give rise to places of liminality and paradox, which are not utterly diluted, but find themselves in constant flux and change.In fact,perception of the impending exhaustion of places provides a social and discursive setting that encourage s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based meanings and identities(Mackenzie 2002).
On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is paradox of place is to turn to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lace and space in geographical thought.As Taylor (1999) points out, space is often conceived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外文文献译文
以汉族旅居者身份书写西藏:快速发展时代的话语、实践与政治
钱俊希,朱竑
地理杂志2016,182(4):418-428
摘要
本文通过对地方问题的讨论,对汉代作家创作的《西藏文集》进行了分析,记录了汉代作家在西藏的旅居经历。最近的人文地理学文献把“地方”概念化为意义的中心。此外,人们还认识到,地方与自我的塑造有关。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汉作家对西藏的地方感如何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塑造自己的身份。在中国本土(neidi)建立一个与所谓的异化和理性生活相对应的生活世界。本研究结合两个理论观点,提出其观点。一方面,它表明,地方是一个表现,凝聚周围建设的话语和生活实践。因此,本文分析了汉作家将西藏划分为一个话语和意义体系的两种方式,以及这些话语是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实践的。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探讨了西藏作为一个地方如何处于地方特殊性与构成中国后改革转型的广阔地域网络之间的张力之中。作家们的文本表现出一种被侵蚀的地方感和被破坏的边缘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以极其含糊和矛盾的方式谈判西藏的不安定转型。
引言
本文以地方理论为基础,对上述有关西藏的著作进行考察。它借鉴了两个平行的理论观点。在实证分析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有人认为,场所不是一个静态的给定,而是一个围绕着被建构的话语和生活实践的表现(Bennett2014)。对于汉族作家来说,他们在西藏的生活世界是由历史特定的话语所介导的,这些话语声称西藏的位置具有“内在”的性质。这些论述反过来又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框架(Martin 2003),它塑造了旅居者的世俗实践,并与其他藏族人接触。同时,地方,特别是在现代性中,天生就容易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化的音译空间的影响。
话语、实践和场所表现
地方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性的网站,是由话语和生活实践同时构建的。
话语和实践都是持续的过程,取决于场所的内部动态和与外部元素的交互。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从来不是一个完成的项目,而是一个事件和事件(Cresswell 2015)。
一方面,地方的经验是由真理主张、意识形态上的话语(Cresswell,2015年)介入引导的。Davis(2005)提供了一个关于地点和话语之间关系的详细理论。在他看来,每一组人都通过从某个地方的某些属性中提取意义,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建立了对某个地方的特定概念化。地点的表现从来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反映出人们倾向于寻找什么。
另一方面,地方也通过与物质性、文化、人和社会关系的实际接触而被生活和实践,这些物质性、文化、人和社会关系编织在一起。Malpas(1999)主张,地方经验不应简单地解释为对地方客观属性的主观、情感反应。相反,“场所是经验结构和可能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alpas 1999,32)。地方呈现出一种习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图式化——行为嵌入其中(Casey 2001)。或者,用Martin(2003)的术语来说,是一个设定基于地点的活动范围的框架。此外,作为一个有组织的习惯的地方是“我们不断付诸行动的东西”(Casey 2001,687,原版斜体)它是由活生生的实践和行动所行动和不断实现的。与这些理论相呼应的是,有人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我们通过紧急和冲突的经历来理解地方(Bendiner-Viani 2013)。总之,基于位置的实践的繁衍性导致了一种涉及情感共鸣和归属的感觉结构。反过来,它又充当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未来的活动和实践可以实现和实施(2010年DAFF)。
关系场所与空间的形成
与此同时,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对地方的潜在“侵蚀”抓住了我们的文化敏感性(Escobar 2001; Castree 2004)。在平凡的生活中,这种紧张往往是由于进步和发展的模糊观念之间的冲突,这导致了同质化和抽象化,以及地方的现实生活,对许多人来说,它体现了自然、包容的生活方式和真实的文化(Davis 2005)。然而,这个地方永远不会被彻底削弱。相反,它正在进行协商和定义(Taylor 1999)。现代性并没有强加一个无缝的、抽象的秩序,而是产生了歧义、矛盾和斗争。外生力量导致了不确定性和悖论的产生,这些地方并没有被完全稀释,而是发现自己在不断的变化和变化中。事实上,对即将耗尽的地方的感知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和散漫的环境,鼓励建立基于地方的意义和身份(Mackenzie 2002)。
理解这种地方悖论的一种方法是在地理思想中转向地方与空间的对立。正如泰勒(1999)指出的,空间通常被认为是普遍的、抽象的和流动的。Taylor(1999)继续提出“地方-空间张力”的概念,以捕捉现代性条件下与地方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在这一公式中,空间通常与一方面由国家领导的集中化项目有关,以将地方纳入统一的政治秩序(Agnew 1987;Taylor 1999)。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主义普遍主义”(Dirlik 1999)。空间被批评为使生命世界和景观合理化,并在世界的几何表示中将位置减少到一个坐标。正如Castree(2004)所警告的,当一个地方被迫向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进程开放时,政治风险是很高的。
虽然空间紧张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发人深省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空间,类似于地方,既不是整体的,也不是必要的,而是生产和执行的。一方面,正如Tuan(1977)所说的那样,空间是一个experiential是构建。它被感知是因为运动和地点之间的关系。空间对地方的破坏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地方被纳入了一个地方网络。有时,如果流动性和运动导致疏离和脱离地方,就会感觉到空间。Tuan还指出,正是“原始空间体验”的根植和定位,促成了空间的抽象概念——换句话说,空间从基于地点的体验中衍生出意义和定义。另一方面,空间与场所是相互构成的,空间是通过嵌入在具体场所中的实践和行动来组装的(阿格纽2005)。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在地方强加话语、愿景和规范,空间感随之产生(Merrifield 1993)。更值得注意的是,Massey(1994)的论文使我们能够欣赏始终开放于网络连接和关系系统的地方。空间被概念化为关系、经验和理解的比例,这些关系、经验和理解比地方规模更大。正如Massey(2005)进一步阐述的,空间是产生场所的相同关系网络的产物,尽管它也为多样性、异质性和差异留出了空间。因此,地方-空间张力可以理解为特殊性和连接网络之间的张力,这可能导致融合和同质化。随着新的联系、新的关系、新的并列不断地出现,空间总是不断地出现,而且永远不会完整。资本扩张和国家集权有助于建立和加强新的联系,但并不是建设空间的唯一因素。
把研究放在:西藏作为生活方式
在西方人的地理想象中,西藏的文化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原始腐败的神权社会向崇高美学和精神世界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汉人对西藏观念的变化相媲美。
突然间,西藏被誉为身份和灵性之泉的潜在锚定者。藏传佛教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汉人皈依,而且主流媒体中的西藏形象也变得高度审美化(Laffite 2014)最近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把西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生活和实践。生活方式,从生活方式迁移的角度来看,与想象和地方消费密切相关(Anderson and Erskine,2014)。
西藏处于一个相对孤立、不受“污染”的地方和它对现代进步和发展的敏感性。
近年来,文学作品在中国受过教育的青年城市专业人士中为西藏的审美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关于西藏的著作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学体裁。它们可以作为理想的数据来源,因为它们包含了丰富、全面的个人轨迹和生活经验的文档。文学作品提供了对世俗实践的详细描述,使人们能够理解话语和实践的相互构成。最后,我们假设书籍长度文本的丰富性很可能暴露出任何其他无缝的一组论述中的不一致和错误。
我们分析的首要目的是阐明西藏作为一个不同的地方而被重新定义的叙述,并认识到它在一个受改革后转型制约的地方网络中的含义。此外,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只是在表达作者的内心世界。相反,后者需要迎合意识形态和更广泛范围的话语。此外,作家、流派和出版商需要与一个新兴市场的利基保持一致,渴望一个崇高的西藏来填补假定的城市人民的精神空白。
代表地:藏族话语
本节考察汉代作家所建构的西藏话语,这些话语在历史上是经过协商的,并使人们能够进一步实践和居住(Hoelscher 2003;Davis 2005)。最重要的是,汉代作家对西藏的话语建构,把西藏融入了一个视域,视域的消失点在于汉代的自我反身性。在这一系列的出版物中,将西藏与内帝的市场转型进行辩证的对比,使其变得清晰易懂。相反,作家们对内蒂的肖像画似乎更能唤起一种空间感,而不是地方感。内地的地方被认为是模糊和抽象的,这种抽象的空间感取决于国家认可的发展观、城市生活经验、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时代精神。
通过对西藏文化和传统的丰富性和活力的赞叹,文本也对迅速发展的内弟缺乏真正的文化。所有的作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描述藏族的风俗、节日和仪式。顾业生和王英也表达了他们对传统藏族手工艺品的热爱,他们认为传统藏族手工艺品抵制标准化和商品化生产。与将物质对象与未受污染的文化和原始智慧联系起来的现代民族志学者一样,作家们热衷于创造一个丰富的藏族传统手工艺品库存,如靴子、手工纸和黄油灯。
最后,汉代作家对西藏独特性的召唤也依赖于(据称)有机的集体生活,而不是内地日益客观的社会性逻辑。内地的道德败坏主题在汉代作家的话语创作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在亲市场社会中的首要地位扭曲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导致了自私自利和陌生人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因此,所谓内地倒转,就是藏族人“纯洁”和“真诚”的人性。在所有的书中,藏人的纯洁性都被热情地颂扬,最重要的是通过庆祝社会生活的活力。特别是顾业生和王颖,在他们的乡村藏族社区之旅中投入了大量的篇幅,并将藏族乡村描绘成一个永恒的、田园诗般的过去,其特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强大的社区联系、不规范的生活节奏以及与传统的牢固联系。
实践场所:另类生活世界中的日常生活
尽管论述为基于场所的体验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概念化,但是场所是通过活生生的行为和实践“付诸行动”的(Casey 2001)。当作家们的话语集中在一个赞美的、浪漫的西藏概念上时,他们实践这些抽象理想的实际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作者们都表示,在西藏逗留期间,他们倾向于生活在相对简朴的状态和对物质产品的简化需求。当宁肯和凌世刚在国家部门工作时,其他五个人在移居西藏后曾参与过高度不稳定的劳动制度。例如,大兵和顾业生作为街头歌手挣得了收入,他们记录了在街头贩卖藏品的旅居者的人气。这些活动产生的收入微薄。相反,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明显地表现出对有纪律的劳动的反抗。
许多藏族人物出现在作家的记述中, 他们更愿意从事新的、进口的追求。一方面,藏人的想象是愿意的,甚至是现代发展的热情接受者,通过嫉妒和欲望的经济运作。由于藏族女孩突然在他们孤立的村庄里出现了一辆车,并且几乎是凭直觉对车的渴望,他们对幸福、无辜的藏族人的形象时常产生疑问。一个藏族男孩在内地遇到一个购物中心时的困惑;藏族儿童非常喜欢汉人带来的糖果和蜡笔。另一方面,嫉妒的经济与幸福的经济同时存在;因此,西藏人民对铁路和公路的建成欣喜若狂,西藏农民转向现代科学以优化农业生产,拉萨居民蜂拥到新建宏伟的火车站观看壮观的景象,庆祝铁路成为西藏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
不出所料,在每一个场合,都是汉人给藏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前者的形象是汉族游客开车进入西藏带来现代消费品的缩影,以及为西藏提供现代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慷慨国家项目。在微妙的方面,这些形象已经恢复了汉族作为一种典型文明的特权地位,藏人应该钦佩和学习(Yeh 2013)。NingKen与藏族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生动地体现了“真实”的位置与对普遍进步的渴望之间的困境:尽管宁的作品来源于学生们对未受污染的藏族人的想象,但他的作品也在口头上强调了现代教育的中心性,并详细记录了他如何批评和劝说几个辍学的学生来维持他们家庭的生计。
文献综述
万玛才旦是一位运用藏汉双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新晋藏族作家兼导演,在多样文化浸染的创作背景以及民族文学的书写立场下,他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说风格。近年来,随着万玛才旦的文学创作在国内国际取得的较高话题度和关注度,国内外学者对其创作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在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简要评析了总体研究现状,并指出当前亟待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发现,关于万玛才旦文学创作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14年以后才有明显增多。其中,国外有关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较少,大多以藏区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方向,如Zhao Yao的Custodians of Tibetan Culture(China Today,2018年67卷第9期),是以藏族文化的保管人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国内对万玛才旦创作的研究稍多,以其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2014至2016年。大体来看,研究方向多集中在民族身份建构与表达、主题、意象与诗性思维、民间叙述四个方面。涉及万玛才旦叙事风格的研究有杨慧仪的《万玛才旦的寓言式小说——在深层意识对精神状态的叙述》(《东吴学术》2015年第4期)、唐红梅和王平的《宁静中的自信与优雅——论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特色与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11月第6期)、韩春萍的《论万玛才旦小说的“意象对话”与诗性思维》(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等,但在这些学术研究中,万玛才旦的叙事风格并非作为主要内容出现,只是偶尔提及。可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高度;而在实践上也有力地推动并拓宽了研究万玛才旦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方便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认识、理解万玛才旦。
通过对万玛才旦小说中“静”叙事的研究,本文认为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实现从分散角度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881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