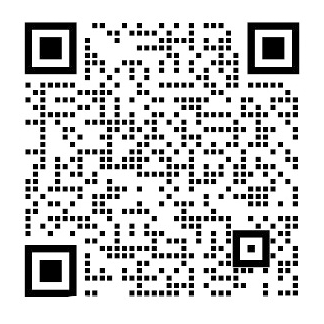澳大利亚旱灾的生活经验:社会和社区的影响
Daniela Stehlik
尽管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干旱,但很少的澳大利亚的研究已经彻底地探索那些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农民家庭生活的经验。正如其他章节有详细的描述,干旱是澳大利亚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曾一度干旱。旱灾成为常见的新闻。例如,当我写这篇文章(2002年7月)时,昆士兰东南部报告了60年来最干燥的季节,7月20日的周末新闻头条写道:”干旱使得歉收,并且在昆士兰中心的第九郡已经被宣布为干旱灾区。”
上世纪90年代的干旱,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已经在的许多领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研究干旱的发生。结合了商品价格的下降,高利率和取款服务(不仅仅是人力服务,还有银行等私营部门的服务),这一经历无可否认地改变了澳大利亚农村的许多传统。作为一种使未来干旱管理更加循证的政策的方法,在这一章中我将以人为中心问两个问题。第一,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在干旱中生存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为什么承认生存经验对于研究干旱的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生活经验是如何被未来的决策者所吸引的呢?
生活或自我经验挑战了一种相对而言普遍适用的方法。公共政策是为大多数人设计的,在巨大的压力以及动荡之下,往往假定一个不存在的同质性。它往往不会挑战“想当然”的假设。然而,承认差异并积极努力融入异质性的政策是创造和交付的挑战。这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决策者、学生和专业人士是如何通过一个生活经验框架来理解干旱,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口述研究,而不是依赖于系统或理论。对于经验现实和理论,有着自我体验的地方。格雷格、路温丝和怀特提出了以下模式,将理论、自我体验和经验现实作为三角形的三个方面,使自我体验能够与理论和经验现实相结合。于是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这种方法。
通过利用被描述为“干旱的社会建构”,在这一章中,我将使用采访的材料作为证据,以使人们能够理解“弹性”的概念——在个人、合作、家庭和社区层面。这种弹性的概念是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它使社会和个人的力量能够应付干旱带来的挑战。
本章首先描述的是弹性的含义,其次是简要地探讨基于证据的政策性质以及依据在获取此类证据方面的重要性。然后简要介绍了开展该分析的研究工作。本章的主要部分引用了一些证据,详细说明了弹性如何应对干旱的挑战,以及这种弹性是如何实现社会凝聚力的。最后,本章对政策制定者如何通过借鉴在澳大利亚农村发展未来政策的经验,使其能够实现这种凝聚力提出了一些广泛的建议。
生活的经验
可以说,只有当干旱实质影响到社区和家庭时,干旱才会成为一场危机,这几乎是常识。然而,上世纪90年代的干旱挑战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即干旱的性质及其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每隔25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异常的干旱。然而在昆士兰,许多农业家庭刚刚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旱灾中恢复过来,那时他们的地区又开始干旱了。另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总的干旱政策旨在应对“正常”干旱,这要求农村人民采取“自力更生”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政策试图“取得平衡”,而不是提供“一刀切”的回应。然而,这些政策也倾向于假定干旱期的长度相对较短,因为没有人准备好多年的持续干旱,正如1990年所经历的那样,在某些地区有6个季节处于干旱状态。人们还认为,干旱是一种相对较慢的现象,人们可以预见到干旱,因此人们可以为此做好准备。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是,“社区”在危机期间以某种方式聚集在一起。事实上,许多政策本身都是基于这种假设的,这种假设依赖于社区的乌托邦理想;也就是说,每个人齐心协力,抛开分歧,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这种理想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随处可见。20世纪90年代的干旱再次挑战了这一点,因为它的长度和广度使得这种潜在的凝聚力变得脆弱。
这些思想假设的挑战来自于1996-1998年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进行的研究中所收集到的关于农业家庭的经验。这个项目由农村工业研究与开发公司以及土地、水资源研究开发公司资助,并由昆士兰中央大学和查尔斯·斯特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建立了这一章的数据。农场家庭项目对1990年代的干旱的经历的描述,是第一次与那些受干旱影响的人一起进行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后见之明或先前的记忆。这使得调查结果更加立竿见影,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反思自己所面临的挑战,在某些情况下非常令人心酸。重要的是,在采访的时候,没有气候学家、政策制定者或农民能够预测干旱将持续多久。当时的一个预测是,对受干旱影响的人们来说,“官方和公众的同情都有所减少”。1988年,希斯考特写道:
我猜想,对那些忽视了这些警告,并对资源管理人员施加更大的官方压力,且要求他们采取管理策略的受害者,公众的同情心会更小。
这项研究,利用了农业世代干旱的象征意义的概念,以及人们如何学习这些符号和如何解读这些符号,建立了一种对干旱的社会建构的模型,这是一种对个人经历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影响。
总之,整个项目的结果是这样的:
bull;家庭是抵御干旱的第一道防线。
bull;男性和女性对于旱灾的经历是不同的。
bull;他们的社区不应被更广泛的社会视为理所当然。
研究还发现,大多数生产者都是这样做的:
bull;争取自力更生
bull;管理风险
bull;努力规划和持续经营。
bull;有环境意识
bull;承担整个农场战略规划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该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的干旱比前几十年更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两个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都在本书中讨论过)——首先是政府政策的转变,其次是更复杂的测量技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现象继续存在。此外,研究发现:
bull;干旱政策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bull;“专家”会造成额外的压力。
bull;人性化服务需要更好的整合
bull;对媒体有某种冷嘲热讽。
bull;澳大利亚乡村感觉与世隔绝,被澳大利亚城市遗弃。
该研究还表明,尽管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容易提前计划,但对很多人来说,采访成为了对诸如以下问题的思考的催化剂:他们会留在这片土地上吗?他们能再次面对这样的经历吗?对他们自己的健康和孩子的健康意味着什么?旱灾如何影响他们为下一代提供的计划?这种个人考虑未来的能力,即使是在绝望的深渊中,也是可以被视为弹性的核心。
弹性化
富有弹性意味着我们可以在震惊或创伤后恢复。这尤其意味着我们已经采取了应对策略,使我们能够成功地从这样的创伤中恢复。国际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在家庭、个人和或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家庭或社会)中能形成弹性。应对策略在个人、家庭和亲属关系网络中各不相同。在干旱时期进行的研究发现,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应对策略;在某些情况下,过分依赖于配偶;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利用多年来建立的友谊网络。对一些人来说,专业的支持在工作中变得很重要。对另一些人来说,对未来的规划可以减少对当下的焦虑。弹性也可以在社区层面得到确认。社会团结和社区互动使城镇或地区在困难时期保持凝聚力。这种弹性超越了有时被称为“交流”或分享利益团体。它是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在危机时刻,它是最有力的体现。来自国际研究的发现,确定了社区支持、社区赋权和社区应对的重要概念,即“社区保护因素的广泛类别,以便当一个社区通过韧性的过程时,它能更成功地掌握逆境和改变”。因此,弹性不仅仅是社会资本,因为它承认这种凝聚力存在矛盾心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不成功,但在它的矛盾心理中,它接纳了社会的所有成员,甚至是那些没有明显的生产性贡献的人。
实现弹性应该是自力更生和可持续性政策背后的指导原则,所有制定的政策都应确保它们建立这种弹性,而不是削弱它。然而,正如在干旱期间进行的研究表明,许多人担心他们不能继续应付正在进行的危机的挑战。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政府对干旱以及对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力感到沮丧,使他们的焦虑更加严重。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对“澳大利亚其他地方”的居民表示失望,那些人居住在大都市地区,对他们来说,干旱可能意味着他们不会像往常那样浇灌花园,这些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就这样,希思科特的预言变成了痛苦的现实。此外,一些人认为媒体也有影响能力。
当然,政府政策也在他们对应对策略的分析中得到了体现。澳大利亚政府的三层(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人们在经济繁荣时期就能理解,随着干旱的持续,政府的政策也变得更加复杂,各级政府也自己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应对这一问题。人类对干旱的反应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地区和农村的“削减开支”和服务的缩减似乎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出现的——它们是社区分裂的催化剂。结果,社会脱节,感觉与现有网络脱节,导致弹性降低,许多人认为,随着危机的继续,“独自行动”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证据的利用
在更详细地讨论证据之前,下面提供了项目的简要概述,数据是如何收集的,以及它的一般发现。
为了捕捉生产的差异,这项研究是在两个不同的区域进行的:位于昆士兰州中部的罗克汉普顿(CQ)附近的牛放牧区,以及新南威尔士西部(NSW)的巴尔拉尔德附近的小麦/羊地区。支持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假设是,男性和女性会有不同的体验,因此项目的建立就是为了捕捉这种差异。首先,在罗克汉普顿和新南威尔士中进行焦点分组。这使得开发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成为可能。然后,在这两个州的56处家庭中,有103人(51名男性和52名女性)接受了采访。在新南威尔士,27名女性和27名男性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和他们自己选择的时间里接受了采访。在罗克汉普顿, 25名女性和24名男性也接受了这样的采访。采访通常持续约两个小时,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和女性会单独面试。同样的问题也被问及。问题包括:他们如何看待和管理干旱、财政影响、生活质量和健康影响、社区支持、政府政策、农场和家庭管理策略。
一旦对采访数据的分析完成,随后对这两个地区的一组较小的家庭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从而促进了更详细的案例研究的发展。最后,在1998年编制了关于RIRDC19的报告,并于1999年出版。
对参与项目的人员的简要介绍提供了该研究的广度。他们的平均年龄在45-49岁之间,在罗克汉普顿地区超过55岁。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农民,平均有25年的财产所有,总共有9000公顷——昆士兰州5138公顷和新南威尔士州,18511公顷。他们有一半的农场完全致力于放牧,只有8个农场使用不到50%的土地用于放牧。在采访时,90%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农场是在干旱地区,虽然下了一点雨,但只有19%的人认为他们的干旱已经被破坏了农业。研究发现,69%的人认为这次旱灾比上世纪80年代更为严重。超过三分之一的干旱要么完全失去了农业生产能力,要么生产力降至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重要的是,约有50%的人表示,他们采取了大规模的销售育种措施,约有15%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广泛”接受了这种选择。
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出版物对这个项目进行分析。这些议题包括性别和干旱;干旱和社区;经济影响;农业结构调整;社会政策和干旱。这些出版物从所有的调查对象那里得到了全部的证据。这个小组对干旱的社会影响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审查,重点是个人、伙伴关系、家庭和社区,以及正在出现的应对策略。通过回答每个案例中的弹性问题,下一节将利用这些受访者的声音,并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尽管在所有案例中都使用了假名。通过这种方式,本章将重点放在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危机的能力上,与此同时,确定与政府政策和人类服务反应相关的因素,在接受采访的人看来,在未来可以更好地管理这些因素。
长期以来,利用证据来更有效地制定政策,是实现满足需要的政策的根本。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理解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即从一个连续体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随机对照试验,从归纳理论中归纳出的“证据连续的证据”。换句话说,人类从各种各样的来源中得出推论。这与一项重要的声明有关:
证据总是证明某些事物(概念性质)的证据,而这又与研究人员的特定优势有关。简而言之,证据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收集到的;它需要被解释和选择。
研究访问使我们对人们生活的了解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入。巴伯认为,没有一种证据优于其他任何证据,而统计“证据”并不是唯一可以预测政策的数据。正如本书中章节的作者所指出的,平衡各种形式的证据,包括社会证据,都能使政策制定得很好。在干旱的情况下,决策者可以得到许多这种性质的证据。然而,如上所述,在我们进行研究之前,很少有人试图系统地询问生产者他们的经验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管理危机。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开始总结我们在采访中所收集到的经验。这部分包括参与我们研究的人的声音。因此,他们是对现实的感知,而不是对他们社会现实的自动快照;因此,“被认为是真实的事物”的表达成为我们的向导。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这些问题是由个人直接经历的,而不是我们可以从外部对它们进行分类,或者我们认为个人应该做出反应。因此,这种反思可以被看作是试图从潜在的混乱中构建秩序的叙述。他们也是考虑人们与实践之间重要联系的方法。需要说的是,人们所说的和他们所做的,不仅在农业实践中,而且在政策实践中也很明显——经常处于脱节的状态。就这一证据而言,我们接受了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向我们叙述的内容。
这些叙述在个人、伙伴关系、家庭和社区层面进行了重组,并提出了创新、适应变化、建立未来和维持社区的主题。
个人管理创新
20世纪90年代的干旱与作为农业管理工具的信息技术的使用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使用信息技术来处理复杂的农场管理方法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他们的资源,而这反过来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策略规划。其中一个例子是,气候信息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特别是在ABC-电视天气的南方振荡指数(SOI)报告中,这种技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些技术要求对生产方式进行“重新思考”,许多受访者解释了他们如何重新接受教育,发展他们以前没有的专业知识。
SOI并不是唯一使用的工具。雨人软件包也成为一个重要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Despite most Australians agreeing that they are only too aware of what drought is, surprisingly little Australian research has been undertaken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through a drought with those most affected—farm families. As other chapters have detailed, drough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ustralian landscape, and most parts of the continent at one time or another are drought declared. Drought is current news. For example, as I write this (July 2002), south-east Queensland is reporting its driest season for 60 years, and The Weekend Bulletin headline on 20 July reads:lsquo;Drought tightens griprsquo;and identifieslsquo;nine shires in Central Queensland that have been drought declaredrsquo;.
The drought of the 1990s, following closely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1980s, and touching many areas, provided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undertake research as it was happening. Combining as it did with falling commodity prices, high interest rates, and with-drawal of services (not just human services, but also private-sector services such as banks), this experience undeniably changed many traditions in rural Australia. As a way of enabling a more evidence-based policy approach to future drought management, in this chapter I will take a people-centred focus by asking two questions.First, what is thelsquo;essencersquo;of living through a drought, for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Second, why is acknowledgement of lived experience important for scholars studying drought and how can these lived experiences be drawn on by the policy-makers of the future?
Lived, or self-experience challenges a universalistic approach that tends to homogenise. Public policy, designed for the many, under great stress and in times of turbulence, often assumes a homogeneity where none exists. It tends not to challenge lsquo;taken for grantedrsquo; assumptions. Yet policy that recognises difference and actively works to incorporate heterogeneity is a challenge to create and to deliver. This chapter suggests that how we as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can come to understand drought through a lived experience framework means that we need to be reflective, insightful and sensitive to language, rather than rely on a system or a theory. There is a place for self experience, as there is for empirical reality and for theory. Greig, Lewins and White suggest the following schema which identifies theory, self experience and empirical reality as three sides of a triangle, an approch which enables self experience to take its rightful place alongside that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reality. We took this approach in our study.
By drawing on what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rought, in this chapter I will use interview material as evidence to enabl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y—at the individual, partnership, family and community levels. This concept of resiliency lies at the heart of social cohesion that in turns enables the communal and individual strength to meet the challenges drought presents.
The chapter is structured first, to identify what is meant by resiliency, and second, to briefly explore the nature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imary sources in developing such evidence. Then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research undertaken to develop this analysis is provided. The major section of the chapter draws on this evidence to detail the way in which resiliency can act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drought and how such resiliency then enables social cohesion. Finally, the chapter makes some broad suggestions as to how policy-makers can themselves enable such cohesion by drawing on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future policy for rural Australia.
Living the experience
It appears almost commonsense to say that drought becomes a crisis only when it affec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yet the drought of the 1990s challenged some deeply held assump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drought and its impact on the rural sector. One such assumption was that exceptional droughts eventuated every 25 years or so, yet in Queensland, many farm families were only just recovering from the drought of the early 1980s, when their districts again became drought declared. Another assumption was that overall drought policy was designed to respond to lsquo;normalrsquo; droughts and this required a lsquo;self-reliancersquo; approach from rural people. In this way, such policies attempted to lsquo;strike a balancersquo;rather than provide a lsquo;one-size-fits-allrsquo; response. However, such policies also tended to assume the length of the drought period as relatively short—no-one was prepared for the many years of ongoing drought as was experienced in the 1990s—as many as six seasons in some areas.It was also assumed that drought was a relatively slow phenomenon and that [it] could be anticipated and thus people could prepare for it. Another deeply held assumption was that lsquo;communityrsquo; is drawn together in some way during times of crisis. Indeed, many policies are themselves predicated on this assumption, one which relies on perhaps utopian ideals of community; that is, of everyone pulling together, putting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working towards a common goal. This ideal could be seen in much media reporting at that time. Again, the drought of the 1990s challenged this as its sheer length and breadth acted to create a fragility around such potential cohesion. It challenged the claim that people behave in a uniform manner as if there was somelsquo;collective mentalityrsquo;that existed simply because people farmed.
The challenges to these assumptions emerged from experiences discussed in data collected during research conducted in Queensland and New South Wales during 1996–1998 with farm families. This project, funded by the Rural Industr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th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at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and Cha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9103],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