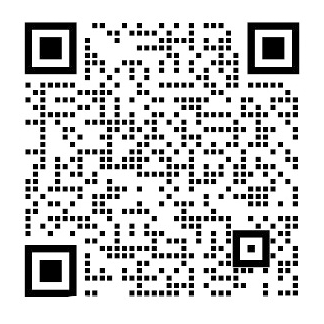治理农村文化:当代中国宗庙的机构、空间与再生产
摘要:本文对农村人民的文化治理机构进行了细致的理解。大多数关于中国农村文化治理的文献都限制了在文化治理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对人民代理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村民被描述为响应国家文化转型的反应性代理人。我认为农村人民的文化治理机构尚未得到充分调查,更深入的理解需要对更广泛的农村社会空间过程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东南新城镇农村传统祠堂的再生产为例,说明农村居民在借鉴农村环境变化的经验的基础上,在促进宗族文化转型方面,有了很大的积极性。国家资助的文化工程,旨在把传统的祖庙改造成文化殿堂、纪念馆和老年活动中心,建设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的农村,实际上是融入了当地人对现代宗族文化的自我发展之中。一方面,新城国家的文化治理受到特定的农村社会空间关系的显著塑造和制约。另一方面,世系群体对寺庙景观的建设有着严格的控制,甚至将改造后的寺庙复制为“延伸”和“影子”寺庙。本文有助于理解农村文化治理中地方人民与国家互动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关键词:农村文化治理;机构;空间;谱系;祖庙;中国
一、引言
农村文化是当代中国国家干预的重要领域。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中国共产党宣布的年度“第一号文件”关注国内发展最紧迫事务的“文件”,不断关注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其主要关注点之一是农民的“低质量”(素质),这部分归因于他们“不满意”道德和卫生条件以及他们对科学和法律的有限认识。在官方话语中,有人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农村人民的精神,智力和道德福利的增强与其实质上改善的物质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大大低于国家的期望。在这种背景下,以农民传统、礼仪和日常生活习惯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经常出现问题,并被有意地作为重建的目标。他们的“落后”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需要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来改变。为了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已经创建了各种国家赞助的项目,如现代艺术和授权的流行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在农村地区的传播被认为是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文化的规范反映了现代世界治理艺术的变化,“文化”被重新评价并强调为一种重要的“政府技术”。正如本文所讨论的,文化治理主要强调为通过文化实现远程治理的不同策略,计划和技术。在中国的背景下,文化这个中国的“文化”一词被动员起来代表文明,区别于无知(没文化)和低级素质。中国政府将文化视为可治理的对象,也是驾驭农村人口、实现理想政治计划的重要工具。农村文化的调节和转变确实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现代化,文明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战略中。在许多情况下,农村文化被客观化,成为经济发展和区域复兴的资源和催化剂。它也被认为是改变农村人民心态和建立现代主体性的有用手段。特别是,这种“文化”概念被政府部署为“迷信”和“落后”的世俗替代品。本文重点介绍了将祠堂转变为“文化”活动空间的国家意识形态。
本文通过对东南温州新城1区传统祠堂再生产的分析,对当代中国农村文化治理进行了考察。宗庙是宗族的象征空间,是一个由同一姓氏的人组成的群体,由于他们的共同祖先而相互联系。根据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农村的主流论述,传统的宗族文化受到政府的改造和改造。新城的许多传统祠堂被改造成文化馆、纪念馆和老年活动中心,本文称之为授权文化空间或改造寺庙。
本文主要通过探讨新城区的宗族成员如何参与、调停和挑战国家文化项目,来探索农村人民代办工作。世系成员不是被动的参与者,但实际上控制着寺庙空间的重新生产。他们积极与国家谈判,并将改造后的寺庙纳入他们自己的现代世系文化发展议程。农村人口中介受当地社会空间条件的影响,包括繁荣的私营经济、世系权力、悠久的文化传统、有限的行政资源等,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治理中的人民中介的分析应超越特定的政治语境。国际农业科学基金会的管理项目,而不是位于更广泛的农村社会空间进程。在本文中,农村被理解为一个关系空间,它由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实践的多个、动态和相互联系的关系构成。农村空间并非仅仅是背景或容器,而是固有地嵌入到具体的治理实践和人民机构的形成中。作为农村空间的主要特征,寺庙是这些混合纠缠的连接,反映了农村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和实践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在介绍实地网站和研究方法之前,我研究了有关治理,农村代理和文化生产的现有文献,主张对农村人民代理机构在国家文化治理中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进行细致的理解。在本文的主体部分,我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宗族文化转型,特别关注农村新城。接下来分析地方政府为何以及如何通过发明多元化的主导话语来促进将祖先寺庙转变为文化大厅,纪念馆和老年人活动中心,这些话语代表传统的祖先寺庙为“落后”,“空洞”和“非法” 空间。尽管如此,国家努力改造宗族寺庙仍受到特定农村社会空间关系的限制,而农村居民则保持着极大的主动性。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通过阐明将授权文化空间重新制作为“扩展”和“阴影”的寺庙空间来讨论农村人民代理机构如何脱颖而出。最后,我总结了本文中提出的关键论点。
二、治理,农村代理和文化生产
在过去二十年中,农村治理研究在英语乡村改革和改变治理艺术的背景下得到了普及。现代国家采用广泛的战略,计划和技术,而不是诉诸武力,以实现对社会的灵活,普遍和有效的监管。在农村地区,它已经从等级控制和强制措施转变为包容性和非集中治理,其中政府,当地社区和个人都参与制定、实施和实施农村政策和计划。治理的力量不是固定在主权国家,也不是由当局掌握。它不会给国家一个中心位置,而只是通过行使而存在。治理农村的“新”艺术激发了学者们对政府与农村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重新思考,包括农村资源、环境、 文化、住房和土地使用。本文以农村文化治理和人民政府为研究对象。
正如西方社会所表明的那样,文化治理与新自由主义的理性联系在一起。它假定了被统治者的代理和自由,并将其纳入治理项目,正如罗斯等人认为“人类的创造力是中心而不是边缘化的”。文化治理鼓励社区倡议和参与,并试图在当局,地方机构和社会团体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它允许非国家代理人和个人管理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而政府通过“指导而不是划船”来实施权力。它通常包含各种话语和意识形态技术,以影响人们的心态,身份和能力,从而促进人们的自治。例如,在许多农村地区广泛宣传自助,社区发展和积极公民身份的观念,以促进社区合作和参与国家计划。
与西方国家一样,当代中国的治理战略和技术也得到了多样化和动员。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考虑到间接和“软”机制和项目,而不是通过胁迫强加国家意志,以规范农村人口的行为和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例如张认为温州民营经济的繁荣有助于形成民主环境。中国农村治理技术的变革也具有历史意义。例如,在中国古代,世系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负责调节农村人口。Faure指出,祖先崇拜仪式被认为是明清帝国向普通民众灌输尊重和忠诚的重要手段。
尽管强调非国家行动者的参与,但治理研究通常集中在从上到下的治理和计算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不同形式的治理似乎是如此系统化,以至于所有的事情都被计算出来并包含在其更广泛的方案中。这样,被治理者的代理似乎是有限的。爱德华兹等人甚至认为,“新”的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以不同名称延续旧政府。以中国的文化治理为例:据记载,中国农村居民是许多国家批准的文化项目(如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但当地人对决策和政策执行几乎没有控制权。在Bruckermann(2016)的山西山村旅游节推广研究中,农村居民仅仅是旅游发展的普通参与者。当地旅游公司和不同级别的国家机构对当地文化的解读有着严格的控制权,在没有充分关注村民异议的情况下,获取了大部分利润。同样地,Ying和Zhou在中国两个著名的历史村庄和旅游目的地(Hongcun和XiDi)的旅游开发中展示了农村当地人有限的“授权”。村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有限,而决策过程由旅游公司、当地干部和精英主导。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农村人民似乎是国家文化转型中温顺的参与者。
与对农村机构的悲观分析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居民不是被动的行动者,而是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进行挑战和谈判,如下面的各种抵抗表现所示。追溯毛泽东时代以来对民间宗教的控制历史,Feuchtwang认为,经济改革后宗教寺庙和宗教仪式的复兴,揭示了当地社区反对国家文化转型的能力。通过抵抗,当地人寻求重新确立宗教自治,并重新获得他们的集体记忆和身份。在贵州少数民族研究中,Yuan等明确研究族群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跨地方文化资源,并将其身份与基督教混为一谈。正如他们所说,混合文化身份的产生是对国家认可的文化统治的抵抗。关于农村治理阻力的类似研究也可以在世界各地关于农村社会运动的新兴文献中找到。
尽管如此,赫伯特 - 柴郡(Herbert-Cheshire)认为,对抵抗的分析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强调了地方机构,其中被统治者仅仅成为国家支配地位的反应者。对抵抗的强调似乎使政府和农村人民相互对立,从而有可能加强对国家 - 社会关系的二元理解。 它忽略了治理主体和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同可能性和形式。 例如,赫伯特 - 柴郡(Herbert-Cheshire)认为人们也可以“服从一项命令,因为它符合他们自己的目标 - 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服从的受害者”。 正如罗斯等人认为,治理永远不是理想的力量,也不排除阻力。 然而,它拒绝将抵抗视为机构与结构之间以及执政对象与主体之间反对的表现。
Chau认为,国家和地方人民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不能通过对支配和抵抗的二元理解来简化。在研究陕西省民间宗教复兴的过程中,当地人不仅抵制国家意识形态,而且积极寻求各地国家机关的官方认可,使他们的宗教活动合法化。这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官方干预,消除“封建迷信”和“落后”等污名。在他的研究中,农村居民机构并没有强调抵抗,而是通过与当地官员的积极协商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分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这种方式,当地的大众宗教融入了主导的文化计划中。在许多其他研究中也记录了积极的农村文化治理地方机构,在这些研究中,被治理者创新地动员主导话语和议程
现有的农村文化治理研究为新城县授权文化空间的生产提供了有关人员与地方政府互动的宝贵见解。首先,国家的文化治理假设人类代理,并将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纳入治理计划。另一方面,“新”治理艺术赋予农村人民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自由权,使他们能够进行谈判,甚至抵制治理主体。然而,最近的研究似乎没有有效地探索实地治理。在中国农村文化治理的大部分现有文献中,对农村人民代理的分析仍局限于文化治理的特定政治背景,其中诸如不同国家代理人等治理主体总是占据特权地位。通过这种方式,农村居民似乎就像国家的文化治理一样,以遵守,合作或抵制的方式行事。相比之下,正如我后来在新城的案例中所探讨的那样,是宗族成员而非政府对祖先庙宇的复制有着坚定的控制权。我认为,对人民机构复杂性的理解,而不是直接局限于具体的管理计划,应该处于农村社会的特定社会空间条件下。
在中国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的巨大转变极大地影响了农村人民对当地国家代理人的理解,反应和谈判的方式。在他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中指出,农村人口通过长期参与农村商品化和旅游以及通过日常经验获得多种规模的动员社会,经济和文化网络的能力。和国家的管理实践相遇。在新城,特定的农村社会空间条件对宗族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主动(传统)生产传统的祖先庙宇。借鉴这些讨论,我还在本文中展望了农村空间的重要性。重点关注农村空间如何融入农村人民代理机构的建设以及具体治理策略和技术的形成。
三、现场位置和方法
本文基于2014年1月至11月中忻城镇沿线景观(再)生产的民族志实地考察。新城位于中国浙江省东部沿海地区,毗邻东海(见 图。1)。 该地区占地面积20.51平方公里,由温州市县级城市瑞安市管理。 根据年度政府报告,新城拥有28个村庄和7个居民社区,2014年人口为77,999人,移民为58,318人。作为温州农村民营经济的主要发源地,新城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增长。。 2014年,新城当地村民年均收入3826.8美元3,远高于中国其他农村地区。
深入的半结构化访谈是为本研究生成定性数据的主要方法。我采访了瑞安博物馆和文化局的7名当地官员,以及新城镇文化中心,统战部和宣传部。对当地官员的采访涉及祖传寺庙的政策和规定,以及新城农村国家赞助的文化项目的实施和评估。此外,还采访了19名血统精英和25名普通血统成员。对这些当地线人的采访包括四个主要方面:(1)重建祖传寺庙作为纪念馆,文化馆和老人活动中心的动机和过程; (2)宗族成员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互动和冲突; (3)纪念馆,文化馆,老人活动中心的日常运作; (4)个人对这些新血统空间的看法和态度。根据这些方面,根据线人的反应和知识,在与线人的对话中收到的新信息以及线人对祖先寺庙重建的经验,提出并修改了具体问题。所有的采访都持续了至少半个小时,其中一些甚至持续了2个小时。大多数采访都是用当地(温州)方言进行的。使用当地方言有助于强调我的“本地”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我对潜在受访者的“访问”。
通过对温州皈依寺庙的在线报纸报道的文本分析,增加了访谈数据。 这些报纸涵盖国家,省和市级新闻,由国有企业经营,作为宣传国家政策和思想的官方平台。 我使用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百度来查找相关报道。 在本文中,我主要审查了7个关于文化馆的在线报告,6个关于纪念馆的报告,以及2个关于温州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报告。 对这些报告的文本分析是对历史上祖先寺庙复制的讨论; 此外,它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可以理解上述的决策,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些信息与新城的农村文化治理密切相关,但很难通过与当地官员的面对面访谈获得。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研究数据也是通过现场观察产生的,该现场在1个文化厅,4个纪念馆和5个老年人活动中心进行。 我的观察主要集中在(1)这些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空间布局,(2)人们的日常休闲活动及其在这些空间中的社会互动,以及(3)在特定节日和时间进行的仪式活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overning rural culture: Agency, spac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ancestral templ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Ningning Chen
ABSTRACT
Abstract:This paper offers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rural peoples agency in cultural governance.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confines the discussion of peoples agency within the given political context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which villagers are described as reactive agents in response to the state-oriente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 argue that rural peoples agency in cultural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fully investigated and a richer understanding require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wider rural socio-spatial processes. In my case study of the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ancestral temples in rural areas of Xincheng Town, southeast China, I show that rural people develop great initiatives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neage culture by drawing on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 changing rural environment. The state-sponsored cultural project, which seeks to convert traditional ancestral temples into cultural halls, memorials and elderly activity centers and to develop a modern, civilized and socialist countryside, is in fact incorporated into the self-development of modern lineage culture by local people.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es cultural governance in Xincheng is significantly shaped and confined by specific rural socio-spatial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lineage groups take firm contro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 landscapes and even reproduce converted temples as lsquo;extendedrsquo; and lsquo;shadowrsquo; templ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and flexibility of local peoples interaction with the state in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By
Ningning Chen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Agency ;Space; Lineage ;Ancestral temple; China
- Introduction
Rural culture is an essential realm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Over the past twelve years, the annual lsquo;No. 1 Documentrsquo;, announ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ttending to the most urgent affairs of domestic development, has continuously given attention to three rural issues (Sannong Wenti), namely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mers. One of its primary concerns is the low lsquo;qualityrsquo; (Suzhi) of peasants, which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ir lsquo;dissatisfyingrsquo; moral and sanitary conditions and their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science and laws (cf. Anagnost, 2004). In the official discourse, it is argued that the enhancement of rural peoples spiritual,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wellbeing over the past decades strikingly contrasts with their substantiallyimproved material lives and has significantly fallen short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tate. In this context, rural cultures, exemplified by traditions, rituals and everyday routines of peasants, are constantly problematized and deliberately targeted for reconstruction. Their lsquo;backwardnessrsquo; is deemed as a great handicap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through active state intervention. A variety of state-sponsored programs such as modern arts and authorized popular culture have been created to promote lsquo;spiritual civilizationrsquo; in the countryside (see Thogersen, 2000; Dynon, 2008). The diffusion of state ideology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rural areas is considered a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national socio-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regul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China reflects the changing arts of governing in modern world, by which lsquo;culturersquo; is re-evaluated and emphasized as an important lsquo;technology of governmentrsquo; (see Bennett, 1995, 1997). Cultural governance, 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mainly emphasized as different sets of strategies, programs and techniques that enable governing at a distance through culture (cf. Miller and Rose, 1990; Rose et al., 2006; Dean, 2010).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Wenhua, the Chinese word for lsquo;culturersquo;, has been mobilized to stand for civilization, distinguishing itself from ignorance (Mei Wenhua) and low Suzhi.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ceives culture as a governable object and also as an essential tool to harness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achieve desirable political schemes. The reg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e have indeed been well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 and socialism (cf. Oakes, 1998; Dynon, 2008). In many contexts, rural culture is objectified and made a resource and catalys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regeneration (see Ying and Zhou, 2007; Li et al., 2014). It is also conceived as a useful means to change the mentality of rural people and forge their modern subjectivities (see Mueggler, 2002; Wang, 2006; Oakes, 2006, 2012). In particular, this idea of lsquo;culturersquo; is deployed by the government as a secular alternative to superstitionrsquo; and lsquo;backwardnessrsquo; (Feuchtwang and Wang, 1991; Yang, 2004; Chau, 2006). This is highlighted in this paper in the state ideology of turning ancestral halls into spaces of lsquo;culturalrsquo;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ancestral temples in Xincheng Town1 in Wenzhou, southeast China. The ancestral temple is a symbolic space of the lineage, a group of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surname and link with one another due to their common paternal ancestors (Szonyi, 2002). According to dominant discourses of the modern, civilized and socialist countryside, traditional lineage culture is subject to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y the government (Yang, 2004). Many traditional ancestral temples in Xincheng are converted into cultural halls, memorials and elderly activity centers, which are called authorized cultural spaces or converted temple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571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