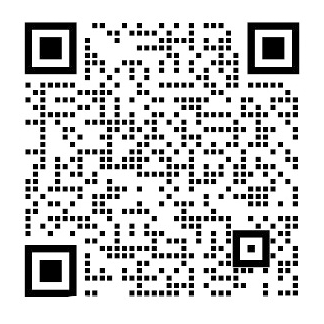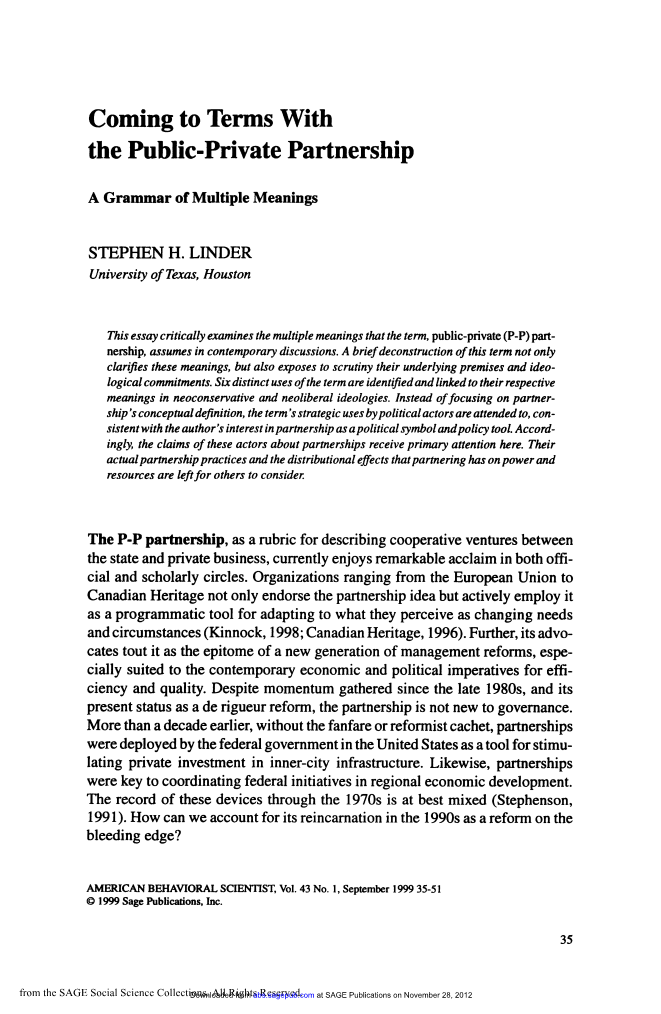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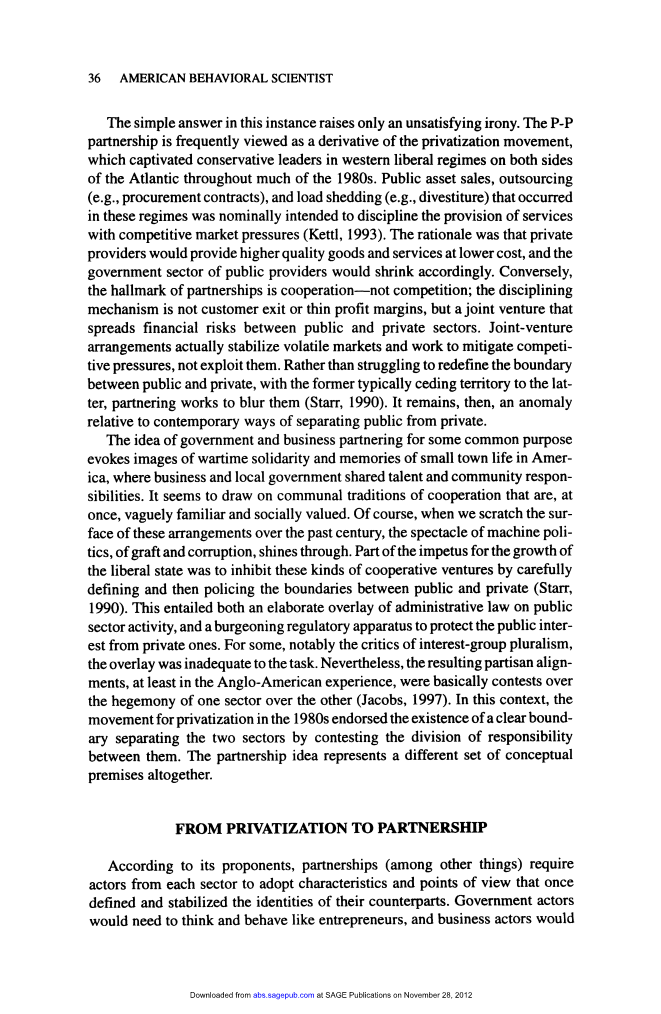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7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使用PPP模式达成协议
多义语法
斯特芬·H·林德
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
本文批判性地考察了PPP这一术语在21世纪讨论中的多重含义。对这一术语的简单解构不仅澄清了这些含义,而且也暴露了对其基本前提和意识形态承诺的审视。在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该术语有六种不同的用法被标识,并与它们各自的含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专注于合作伙伴的概念定义,政治行动者对术语战略上使用,符合当权者在合伙关系的利益,把它作为一个政治象征和政策工具。因此,这些行动者关于合伙关系的主张在这里受到了主要关注。他们的实际伙伴在实践和合作伙伴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资源影响六代其他人去考虑。
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作为描述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合作的标准,目前在官方和学术界都享有显著的赞誉。从欧盟到加拿大传统的组织不仅赞同这种伙伴关系理念,而且积极利用它作为一种方案工具,以适应他们认为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环境(Kinnock,1998年;Canadian Heritage,1996)。此外,它的倡导者们还吹捧它是新一代管理改革的缩影,特别适合当代经济和政治对效率和质量的要求。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势头强劲,而且目前已成为一项常规改革,但这种伙伴关系对治理来说并不新颖。十多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在没有鼓吹或改革派标志的情况下,部署了伙伴关系,作为刺激私人投资于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工具。同样,伙伴关系是协调联邦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举措的关键。这些手段在19世纪70年代的记录充其量是喜忧参半的(Stephenson,1991)。我们怎么能把它在1990年代的重新产生解释为一个处于流血边缘的改革呢?
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回答只会带来一种令人不满意的讽刺。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经常被视为私有化运动的一个衍生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西洋两岸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权中的保守派领导人尤为青睐这种模式。在这些政权中发生的公共资产销售、外包(如采购合同)和减载(如资产剥离)名义上是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压力(Kettl,1993)下约束服务的提供。其理由是,私营供应商将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而公共供应商的政府部门将相应缩减。相反,伙伴关系的标志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约束机制不是客户退出或缩减利润,而是建立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分散金融风险的合资项目。公私合营的安排实际上稳定了动荡的市场,并努力缓解竞争压力,而不是利用它们。与其努力重新定义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前者通常会将领土割让给后者,不如通过合作来模糊它们(Starr,1990)。因此,它仍然是一种与当代公私分离方式相关的异常现象。
政府和商业伙伴关系的概念,为了一些常见的目的,唤起了战时团结和美国小镇生活的回忆,在美国,商业和地方政府共享人才和社区责任。它似乎借鉴了一些共同的合作传统,这些传统一下子就被以模糊的样子熟悉并受到社会的重视。当然,当我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揭开这些安排的面纱时,机器政治、贪污腐败的景象就大放异彩。自由主义国家发展的一部分动力是通过仔细界定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然后对其进行监管,从而抑制此类合作企业(Starr,1990)。这既需要对公共部门活动的行政法进行详尽的覆盖,也需要一个新兴的监管机构来保护公共利益不受私人利益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特别是对利益集团多元化的批评者来说,这项工作不足以完成。然而,由此产生的党派联盟,至少在英美经验中,基本上是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霸权的争夺(Jacobs,1997)。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通过对两个部门之间的责任划分提出质疑,认可了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明确的界限。伙伴关系的概念完全代表了一组不同的概念前提。
从私有化到合作伙伴制
根据其支持者的说法,伙伴关系(除其他外)要求各部门的行动者采纳已经被确定了特征与身份的观点。政府行动者需要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和行为,而商业行动者则需要需要考虑公众利益,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这儿,为定义角色和制定企业与政府之间交往规则所做的精细划分被忽略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相互作用的对抗性的动力。此外,在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国家,为适应公私合营模式,改变行政程序的法律条款,使得国内服务专业化、制度化公共问责制度。例如,在意大利,国内服务改革正在消除公共部门职业与私营部门就业的许多特征(Supiot,1996)。规则制定程序,曾经是美国指挥和控制法规的核心,已经被修改为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为中心,(协商规则制定法,1990年)。简而言之,在战后自由主义国家与其自由市场对手之间的竞争下,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合作伙伴关系逐渐变得和谐。
更一般地说,在福利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中,定义公共与私人二元分离的参照点已经被混淆,多种部门观点的复杂性,包括民间、亲密和对话领域,这些观点都是以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的独特概念为基础的。现在,使用“公共”和“私人”这两个术语,可以看出各种社会差异,而不是所有这些都转化为对霸权的两极斗争(Weintraub,1997)。如果说伙伴关系是另一种反自由主义的努力,通过改变其职能来缩小国家,那就是误解了伙伴关系理念的重要性。首先,比喻性地通过缩小一个部门来扩大另一个部门不再适用(如果曾经这样做的话),因为部门本身的含义正在改变(Feigenbaum、Hamnett和Henig,1998)。第二,伙伴关系倡导为公共管理者讨论新的角色和创新工具,利用私人资本进行政策举措。早期关于政府效率低下和项目浪费的私有化言论,虽然其党派人士仍然活跃(Jack, Phillips, amp; The Robert Phillips Group, 1993,1993),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围绕伙伴关系概念重新产生的部分热情反映出新的可能性和不断变化的一致性。正如我稍后将要讨论的,尽管是无意识的,这种感觉反映了在思想上以及概念上治理格局的更大变化。
私有化作为一个纲领性运动的驱动力通常归因于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和保守的政治家,他们共同反对自由福利国家(Starr,1988)。在完全私有化似乎难以处理的领域,合伙制作为一种衍生改革而出现,可能是由于涉及产权转让的技术问题。如果统计人员的职责必须延伸到某些商品和服务,那么逻辑是,交付应该通过业务中介安排。然而,一旦这些意识形态被详细考虑,就会产生复杂的情况。私有化背后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作为葡萄牙思想的地位,它汇集了务实的改革者和不同阶层的理论家。当我们解开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之间的各种推理路线时,我们发现了伙伴关系旨在体现的独特承诺。这些意识形态中最突出的是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这些将作为伙伴关系意义的来源加以探讨。因此,伙伴关系本身的概念将显得千变万化,使其不易接受简单的技术或方案定义。
除了部门边界的丧失及其伴随的逻辑,以及沿着新的断层线的意识形态分裂之外,第三个对P-P伙伴关系的修辞和意义的影响来自于管理改革的倡导者。它们提供了操作细节和组织流程,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治理。这些举措的范围与战后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努力相抗衡。英国公共服务部将伙伴关系的理念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可能是为了与准自治政府组织中不幸的托利党实验保持距离(即,半官方;英国议会,1997年)。在美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运动是重新设计政府;前提和文字性语言可以在主要管理咨询公司的宣传材料中找到(Reijniers,1994;Jack等人,1993;Apen、Benicewicz和Laia,1994)。同样,政府和商业组织在适应全球经济、新的通信技术和日益增长的客户质量压力方面表现出相似的需求。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结构灵活,以结果为导向的流程和客户服务伦理(加拿大公私合作委员会,1996年;国家公私合作理事会,1997年)。然后,合作成为共同克服仅存的几个无法解决的差异的工具。然而,一旦我们增加了意识形态背景,这些前瞻性的改革就显得不那么有先见之明,更具工具性和机会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的论点将当代伙伴关系理念的更新与三种变化联系起来。在最抽象的层面上,有大量的理论工作,批判性地阐述并扩展了传统的二元部门划分的复杂性,从经济学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一思想开启了对独特制度领域的公众话语,激发了社会秩序的新观念。实际上,公共和私人的旧划分失去了其自然外观,并呈现出早期过时的艺术品的特征(Wolfe,1997)。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政治价值观和承诺的影响引发了当代意识形态的分裂,至少在北大西洋边界的自由宪政政权中是如此。在19世纪80年代,保守党在这些政权中的统治地位为他们的理论基础增加了地位和实践经验(Giddens,1994)。这些,加上官方的责任和错误,有助于分裂成派系的运动,但同时,增加了对进步时代理想和战后福利国家的中间主义方法的似是而非的选择。最后,在务实的层面上 到20世纪90年代初,管理改革的趋势已经从领导和行为原则转向更加注重灵活性和创新,加强伙伴关系理想(Reijniers,1994年)。
合伙的多重含义
有了这些背景特征,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去理清P-P伙伴关系在当代讨论中的意义。正如标题所暗示的,这里采用了一种解构的形式来解构这个词的各种含义,并将它们的一些基本前提和意识形态承诺暴露在严格审查之下。解构主义策略隐含在前面的论据中,注重语境的概念性、意识形态性和语用性,以澄清意义的产生。然而,我在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的意图要比全面的后结构主义分析所承认的要温和得多。我更愿意依赖某些演员对这个词的讨论性使用,而不是依靠唤起这个词的叙述性图像和故事,因为我的兴趣更多地倾向于政治思想和政策工具,而不是代表性策略。同样,关于合作关系的主张将受到关注,而不是合作关系实践,因为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更感兴趣的是概念上的澄清,而不是合作关系可能需要的权力或排除模式的运作(见Handler,1996年)。最后,我的澄清工作不会超出价值承诺的范围。关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谱系的问题还有一段时间。
要绘制散点地形图,首先要确定一些可以作为参考点的地标性用法,然后根据几个固定的思想投影确定它们的方向。每一种用法的意义,不是过于强调隐喻,来自于澄清它相对于其他用法的位置,并了解它的思想方位。在这个术语中,P-P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政策手段,至少有六种不同的用法可以作为参考点。这些不是相互排斥的定义范畴,可能有助于某些分类目的,而是某些行动者在申请或采用该术语时使用该术语所附带的简单含义。下一步是定位这些相对于几个意识形态,并确定他们最可能的附件。
意识形态参考
这里所代表的两个意识形态都有新的前缀,这表明了与西方政治经验中充分阐述的各自的制度化形式的自觉分裂。也许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近地天体都回归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在他们看来,更纯粹的形式。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反对所谓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战后欧洲工党和新政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尽管在哲学上与洛克的个人主义相一致,但它似乎归功于苏格兰的启蒙思想(由于史密斯和休谟),即通过所有权和市场交换实现道德再生。它对市场激励所促进的自发社会协调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哈耶克。然而,它与当代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明显致力于材料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杜威语用主义者的代理意识。
这种代理感与其说是基于激进的左派和右派所倡导的完美性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对人类创造力及其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的信仰。尽管新自由主义几乎不属于集体主义,而且对家长主义的警惕也可以理解,但它与克罗利(1987)在韦伯的进步时代作品中发现的自由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通常被归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对于韦伯来说,进步依赖于创新,创新来自社会实验。新自由主义者会同意社会变革可以通过组织手段进行设计,但比起BeatriceWebb的工业规划者,他们更希望哈耶克的市场企业家。尽管如此,他们都认为设计新颖的组织机制,而不是社区团结、公民美德或个人培训是取得进展的关键。当然,在不同程度上,这两者都会求助于政府作为赞助商或裁判。
第二种意识形态是新保守主义,其形成部分原因是对传统保守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和宗教性的不满。尽管保守主义的新观点与它的父母有着共同的伯克恩根源,但它代表了一种奇怪的对传统所传达的沉积如山的知识的尊重的混合体,以一个洛克自由主义者对自力更生和商业的信仰作为人类自由的保证者。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要努力加强当地的文化机构,这些机构灌输传统价值观,即家庭、社区教堂和公民协会,同时反对权力集中(经济或政治)破坏这些价值观或其复制的社会秩序。自由福利国家以权利取代沙漠,以法律主义取代美德,以家长主义取代自主,有效地侵蚀了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础。同样,大公司为了促进无限的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营销,取代了自我约束的即时满足、谨慎生活方式的名人生活方式和社区服务的占有利己主义。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如果它选择促进适当的文化附件和机构,或者只是选择撤回其替代者,都可以成为盟友。
这两种新意识形态通常都聚集在新右翼的旗帜下,作为对传统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市场,如果有的话,是一种去传统化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而不是稳定。在全球市场自由交易的参与者很可能会暴露在对其价值观具有腐蚀性的情绪和实践中。此外,消费者寻求满足她的胃口的行为与履行社区义务的公民截然不同。我们期望消费者向外寻找机会和价格信号,而公民向内寻找指向道路的道德指南针。不能保证这两种观点是一致的。新权利的形成使美德与欲望相悖,并相信前者会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只能让事情变得更艰难。
当然,现代性的一个方面是相信自我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消费者,我们通过自我增值来适应社会角色的复杂性和社会分化。现代自由主义提供了另外两个补充这一点的解决方案。首先,道德情操可以由品味而非美德来塑造,巧妙地消除了矛盾的一面。这是边沁送给现代人的礼物。第二,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一个私人的金钱和消费领域,一个公共的权力和公民领域;我们似乎应该归功于自然法契约理论(Gobetti,1997年)。新的右派在这两种解决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60997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