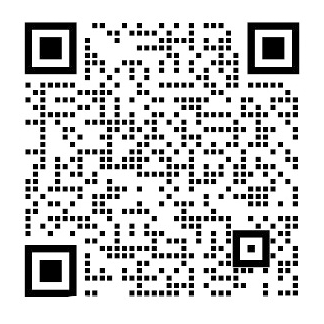背包客民族志
原文作者 Anders Sorensen
Centre For Regional and Tourism Research, Denmark
摘要:本文对国际背包客的旅游文化进行了民族志研究。描述了他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勾勒出旅游文化概念的轮廓,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背包客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并重点分析了道路状况这一关键现象。对背包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现象内部变化的理解。变化因素的例子包括旅游指南、短期背包客,尤其是互联网。这项研究证明了一个动态的文化概念的优点,即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会被社会环境激活。
关键词:背包客; 廉价旅行者;旅游文化;文化概念
一、背包旅游文化
这项研究是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自1990年以来,作者已经记录了23个月的参与者在背包客中的观察。八段时间的实地考察,从两个月到七个月,涵盖了东非、印度、中东、北非和东南亚,而欧洲则被包括在众多短暂的背包客领域。这使得主要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仍然没有被发现。其他研究部分弥补了这一缺陷澳大利亚研究得很好而美洲几乎是未知的。关于作者没有探索的地区的信息已经从各种其他来源(旅游指南、背包客、旅游作品等)收集到,但这项研究不能声称原始数据的全球范围。
在人种学田野调查中,重点是探索社会或文化现象的本质,而不是渴望检验关于这些现象的假设(阿特金森和哈默斯利1994:248)。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有效性建立在与被调查者的互动上。以及由此获得的社会和文化洞察力。通常,人种学的主题是由地理位置来界定的,或者是由一个明确界定的群体内有凝聚力的持续的社会互动来界定的,个体的变化是有限的。
背包客不符合这两个界限。他们不是在一个稳定的群体中进行长期的社会互动,无论是流动的还是定居的,而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组成群体中进行即兴的社会互动,个体不断地发生广泛的变化。在方法论上,这使得我们不可能坚持传统的人种学田野调查框架,即与给定的一组线人进行长期的社会互动和观察。背包客社区的非属地化意味着,与少数人的长期互动不同,实地调查必须围绕着与多数人的即兴互动展开。这使得实地调查比传统的人种学实地调查更依赖于访谈和其他类型的密集信息提取。
到目前为止,实地调查已经完成了134次正式的、半结构化的访谈,时间从45分钟到3小时不等;22次半正式的讨论会,时间从1到7个背包客,时间从1到2个半小时不等。除此之外,还必须增加数百次以扩大对话形式进行的半正式和非正式访谈。在交通期间,或在远足(旅行、徒步旅行等)期间,在受欢迎的目的地和较外围的目的地的住宿设施、餐馆、酒吧等处进行采访。在大多数情况下,潜在的告密者与背包客社区的联系可以通过外表、行为或同伙立即辨别出来。在少数情况下,初步询问是必要的,以验证一个人作为一个潜在的告密者。进来在所有的正式访谈案例和几乎所有的延伸对话案例中,作者都有意直截了当地谈到正在进行的研究以及他作为背包客和研究者的双重角色。虽然这一立场最初是一个研究伦理问题,但它也产生了研究效益,因为认识到他们正在研究往往引发有趣的思考和审议的线人。许多人对这项研究表示了兴趣,并在采访期间或之后询问了迄今为止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初步调查结果或解释与他们分享。这反过来又会引起线人的评论,有些会引起激烈的辩论。在许多情况下,最有趣的数据是在采访正式结束后曝光的。
访谈和延伸对话构成了实地调查材料的有形内容。然而,对背包客旅游文化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背包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无数观察和互动以及参与他们的道路文化。
二、识别背包客
无论是通俗的还是在研究文献中,背包客最常被描述为具有灵活行程的多目的地长距离旅行中的自组织愉悦游客,超出了通常可以适应周期性假日模式的范围。
然而,这一描述仅作为指导,不能用于客观区分背包客和其他游客,因为只有少数人符合整个行程的所有参数。
一方面,有些人现在带着“入门包”出发,例如包括机票、机场接送、转机和在门户城市的初步住宿。再加上大多数背包客在旅途中会购买有组织的短途旅行、旅行、徒步旅行等,这使得自组织有点值得商榷。有些旅行包括工作咒语(Riley 1988;Uriely和Reichel 2000),这使得快乐参数同样值得商榷。时间参数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长途旅行的想法是高度个人化的。唯一的共同特点是“旅行”,灵活的多目的地行程。甚至连这一点也在不断地被讨论背包客。所以,背包客不能用明确的标准来定义。皮尔斯认为,他们最好用社会而不是经济或人口统计学的术语来定义,并指出了一些标准,如对预算住宿的偏好,对满足其他背包客的重视,以及独立灵活的旅行计划(在Ross 1997a中引用)。如果被视为一个社会范畴,术语背包客提供了分析性质,以补充文献中主要描述性使用的术语。因为尽管许多不符合描述特征,但这些描述了背包客倾向于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形成了旅行意识形态的轮廓。从内部人士的角度来看,这个类别是有意义的。背包客既是一种个体认知,又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身份认同,与其说是一种定义,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它显然是民族志研究的对象。
三、人口和社会基础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民族代表,背包客仍然主要是西方血统。绝大多数来自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欧。大多数欧洲人来自北欧,而地中海欧洲的代表性不足,考虑到人口规模,美国也是如此。以色列背包客也有很多。此外,日本背包客的数量似乎在减少成长。好几个关于性别分布的研究报告(Loker-Murphy 1996;Loker-Murphy and Pearce 1995;Murphy 2001;Riley 1988;Ross 1997a),但结果各不相同。澳大利亚的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相当,而作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显示,男性占60/40的优势比例,在某些地区可能略高一些。
绝大多数背包客年龄在18-33岁之间。人们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属于22-27岁年龄组,27岁以上的人比22岁以下的人多。这与类似的印象很吻合,很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在开始他们的第一次背包旅行之前已经完成了教育并工作了几年。然而,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十年来的实地观察表明,到遥远的地方去旅游越来越普遍。尽管如此,背包客的教育水平仍相当于或高于其原籍国的一般水平。很大一部分人拥有学位。此外,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这往往是一个尚未完成的问题;大多数人打算在旅行后开始或完成学业。
当代背包客不适合描述漂泊者,离经叛道者和逃犯描绘在一些出版物从70年代(科恩1972年,1973年;十有1974年)。总的来说,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支柱,暂时离开富裕的生活,但有着明确和坚定的意愿,要回归“正常”生活。这种坚定性在预定的旅行时间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固定的返程日期,通常由他们的机票来定义。即使是那些宣称自己不受约束的人,如果受到足够的刺激,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会显示一个固定的最新返回日期。通常的旅行时间在两个半月到18个月之间;很少有旅行时间更长。事实上,超过12个月的旅行并不多,而4到8个月的旅行间隔占了大多数。两个半月的下限也标志着“真正的”背包客和那些喜欢旅行但能适应工作/假期的人之间的社会界限模式。暂时然而,正常的生活是暂停的。许多背包客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刚毕业、结婚或离婚、工作间隙;当他们被问及为什么旅行时,这样的解释经常出现(Riley 1988)。因此,许多背包旅游属于一个生命周期的过渡期。然而,虽然这可以得出结论,过渡情况导致了旅行(格拉伯恩1989年;赖利1988年),作者发现,反向因果关系适用。深入采访发现,虽然过渡时期的情况是真的,但通常情况恰恰相反:旅行愿望让人辞职,导致分手,等等。来自英国的马克这样解释:
这是一个现在或永远的问题。自从几年前大学毕业以来,我赚了不少钱,所以我可以负担得起旅行。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因为十年后,我可能会和妻子、孩子、抵押贷款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绑在一起。谁知道十年后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不同地方或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快消失,他们都变得或多或少像我们。如果你想看到任何不同于我们西方国家的东西,你必须在它消失之前赶快做。
马克声明中的“消失的世界”与许多旅游广告中的紧迫感产生了共鸣。然而,这一拉动因素与紧迫性的推动因素相匹配,以在为时已晚之前超越常态。马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通常过渡期是自我造成的,是由旅行的欲望带来的。事实上,这更符合逻辑,因为旅行通常是有计划的冒险。很少有人拥有必要的经济手段,使他们能够迅速实现长期的决策绊倒。所以,许多背包客旅行可以被描述为自我强加的过渡期,对许多人来说,自我强加的通行仪式。对背包旅游的这种理解与当代学术界对现代社会中的仪式和通过仪式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认为自我强加的成人仪式是唯一的解释是错误的。
四、文化观念与短暂背包客
虽然文化一词在旅游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有趣的是,在旅游者及其行为的研究中很少使用这样的概念。旅游文化的概念很少出现在研究文献中,当使用时(阿德勒1985;福斯特1986;纳什1979),这个词最常出现在描述。它很少被用来分析、解释或解释旅游业的各个方面行为。它似乎有理由认为,并非所有这样的行为都可以由家庭带来的规范和价值观来解释,也可以由家庭带来的价值观来解释。旅游业的极限维度(Lett 1983;Wagner 1977)。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识别出建立在游客互动中的社会结构、规范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概念可能是适用的,前提是旅游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产生了意义,反过来又影响到规范、价值观、行为和社会行为。
至于背包客,这种旅游文化概念提供了一个相关的框架,尤其是考虑到许多人大部分时间都与背包客同伴在一起。在整个旅行过程中,这些都会不断地被替换,但是这些替换具有相同的旅游特征:强调自我组织和游牧主义,计划灵活,易于快速调整换衣服。那里这是双重约束。一方面,背包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旅行方式,作为陌生地方的陌生人,同行的背包客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另一方面,旅行方式也是他们唯一确定的共同点。因此,谈话主要集中在旅行上。
然而,背包客文化不属于这两种文化。既没有固定的地点也没有固定的群体来界定它:这种文化既没有定位也没有界限。因此,为了通过文化的概念来理解背包客,有必要超越“文化的放置”,而是让这个概念允许文化“发生”在任何地方。换言之,必须允许文化“旅行”(Clifford 1997)。习惯上,道路文化的概念是经验性地建立和描述的,即
描述属于某一类别的个人的文化(Adler 1985;Mukerji 1978;Riley 1988)。相比较而言,本研究所采用的背包客旅游文化概念,使得背包客旅游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范畴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
(一)旅游文化轨迹
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大多数背包客都欣然接受旅游包含了旅游的元素,或者是一种旅游方式。这些发现与Riley的发现相反,Riley发现所有长期旅行者都强烈拒绝旅游标签(1988:322)。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她的线人已经旅行了一年多。另一个解释是,自上世纪中叶莱利的研究以来,背包旅游的发展和制度化从80年代以来,旅游业和旅游业是分开的、不同的事业,这一形象越来越难以维持。
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赖利和作者的发现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程度的问题。因为,尽管大多数背包客在旅行中承认了旅游业的一个方面,但他们仍然保持着旅行者和游客之间的区别。他们常常把自己定位为一种更好的旅游模式的代表,从而保持了背包客“我们”和游客“其他”之间的区别。背包客通常认为,他们自己安排事情,而游客是被引导或放牧的,而且,与游客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走出老路,找到未受破坏的地方,并对该地区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Desforges 1998)。这样,这种文化加强了背包客的重要性。
强调游牧、自我组织和自力更生。因此,并非所有的旅行方式都传达了平等的地位,而且陆路旅行比飞行传达了更多的地位,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广受欢迎的陆路连接着人们喜爱的目的地,形成了主要的小径,许多背包客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些小径上度过。在这里,可以找到旅馆、餐馆和其他服务设施。旅游指南中的建议加强了主要路线的受欢迎程度,几乎每个背包客都会携带这些建议。另外,“小道消息”(Murphy 2001),背包客之间的信息和故事交流,其本身将他们的社会结构重构为身份,加强了某些路线的流行。
然而,许多背包客花了一些时间离开主要的小径。这一模式在文化上得到了加强,因为离开典型路线旅行、体验艰辛、或许发现新地方,都可以通过与其他人在主要小径上分享信息而转化为道路状态。新地方的发现意味着这些痕迹不是静止的。其他人可能会决定使用这些信息,如果有足够的信息,为背包客提供服务的旅馆和餐馆可能会开业,服务基础设施也会出现,新的线索也会建立起来。通常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另一方面,新的背包客路线和目的地通常就是这样形成的。很明显,小径的变化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政治变化、内乱、恐怖主义或战争可能会关闭或阻止它们的使用;相反,恢复和平、改善基础设施或政策变化可能(重新)开放背包客小径。
(二)短期背包客
变化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短期背包客,背包客旅游的实践、制度和文化方面相互影响。这些人喜欢背包旅行,但在周期性假期模式的时间限制内。他们的行为就像普通的背包客:他们与其他背包客进行社交互动,呆在同一个地方,沿着同一条小径旅行,尽管他们在旅途中自然会少走几步路短途旅行-术语背包客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然而,最近的实地调查数据和信息来自专业旅行社表明这一部分增长强劲,可能比一般的背包旅游增长强劲。部分原因可能是长途机票价格下降。显然,这对于背包客旅游业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短期游客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由于返程机票在他们的旅行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更大,航空旅行价格的降低导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BACKPACKER ETHNOGRAPHY
Anders Soslash;rensen
Centre For Regional and Tourism Research, Denmark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travel culture of international backpackers. Their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re described, the contours of a concept of tourism culture are delineated, and on that basis, that of backpackers is outlined,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key phenomenon of road status. The analysis of backpacker tourism as a culture furthers the comprehension of change within the phenomenon. Examples of factors of change include the guidebooks, the short-term backpackers, and in particular the internet.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merit of a dynamic concept of culture where culture takes place whenever activated by social circumstances. Keywords: backpackers, budget travelers, travel culture, concepts of culture, ethnography. 2003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TRODUCTION
To me, Khao San Road ha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al Thailand. Itrsquo;s shops and hotels and restaurants and loads of people calling themselves travelers but being ripped off all the same. But itrsquo;s got whatever you need and some great food, and itrsquo;s a good place to meet other travelers. I always hang out in Khao San Road when Irsquo;m in Bangkok (Timothy from Germany).
The Khao San Road area in Bangkok is probably the epidome of the backpacker ghetto. South East Asia is the most popular region for international backpackers; Bangkok is their main gateway to the region; and when there, most head for the Khao San Road. The development is spectacular: from two guesthouses in the early 80s, there are now several hundred in the area (Cummings and Martin 2001:231) along with restaurants, travel agents, internet cafes, bookshops, and more. Thus, the Khao San Road area strikingly illustrates the worldwide growth of backpacker tourism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Even so, few figures document this growth, although it is estimated that backpackers account for 8%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o Australia (Loker-Murphy and Pearce 1995), for the phenomenon escapes the categories of conventional tourism statistics. Nevertheless, in lieu of quantitative confirmation, various qualitative factors expose its development, including a growing number of backpacker guidebooks, a growing service infrastruc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ccessories shops,travel advertising, web pages and, of course, the sheer visibility of backpacker tourism at the popular destinations.
The development is noted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n 1972, Cohen depicted the drifters of the 60s who shunned the tourism sector in their quest for immersion in the host societies (1972:175–77). However, as early as 1973, Cohen described the Vermassung (growing mass consumption) of drifter-tourism and how it supported the rise of an alternative service infrastructure, a development also observed by Turner and Ash (1975).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ackpacker infrastructure, destinations, and routes is further described by Cohen (1982), Pryer (1997) and Riley (1988).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has not been accompanied by homogeneity among the users of the backpacker facilities. On the contrary, this mode of tourism seems more composite and multifaceted than ever. Even casual observation at favorite locations such as Khao San Road confirms this. In this small area one can observe the interactions and groupings of disparate characters such as well-educated young Westerners on extended leave from affluent society, high school graduates on gap year travels, Israelis fresh out of military service, university students on holiday or sabbatical leave, young Japanese in rite-ofpassage attire, ordinary holidaymakers, (ex-) volunteers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and the like. The heterogeneity is manifest, whether viewed in terms of nationality, age, purpose, motivation, organization of trip, or life cycle standing.Scholars have commented on aspects of this heterogeneity (LokerMurphy 1996; Murphy 2001; Ross 1997b; Scheyvens 2002; Soslash;rensen 1999), and Uriely, Yonay and Simchai (2002) convincingly question the notion of backpacking as a distinct and homogeneous category. Indeed, the variation and fractionation make it all but impossible to subsume all the above-mentioned individuals and groupings under one uniform category, for it would be so broad as to be devoid of significance. Nevertheless, if questioned, most of these individuals will generally acknowledge that they are backpackers or (budget) travelers, and even those who do not accept such labels still relate or react to them. The ex- or implicit recognition of the notions carries a significance that reaches beyond an implicit dissociation from a tourist stereotype. For with varying degree and intensity, these individuals connect to a shared frame of reference whether this is a matter of identity, philosophy, sense of belonging, or sentiments of shared values, and their
partitioned and fractioned interaction produces meaning, which influences norms, values, conduct,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social being.
This complex—the human systems of meaning and difference (Clifford 1997:3)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diversity (rather than the replication of uniformity) which produces structures of meaning (Hannerz 1990: 237)—is at the core of recent advances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ulture. Therefore, it would seem profitable to utilize a concept of cultur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backpacker tourism, whereby backpacker culture is not only seen as the culture of people categorized as backpackers but is also recognized as essential in the continuous re-creation of the category of the backpacker.
BACKPACKER TRAVEL CULTURE
The study is based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Since 1990, the author has logged 23 month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mong backpa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1052],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