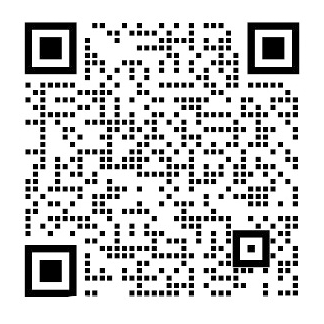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1 (2021) 15–28
Contents lists available at ScienceDirect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homepage: www.keaipublishing.com/en/journals/china-economic-quarterly- international
The heterogeneous growth effect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irm-level evidence for a global sample of cities☆
Josacute;e-Daniel Reyes a, Mark Roberts a, Lixin Colin Xu b,*
a World Bank, USA
b World Bank, and CCER, PKU, USA
A R T I C L E I N F O
JEL classification:
D9 G3 H1 H2 H7 L5 O1
Keywords:
Firm growth Productivity growth Institutions Corrup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A B S T R A C T
Using firm-level data covering 709 cities in 128 countries, we examine the role of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busines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in explaining firm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We find basic protection (with corruption as an element), access to fi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a strong agglomeration environment to be critically important. By contrast, human capital and a list of refined business environment variables related to labor regulations, tax, and land access are unimportant. We also find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vary according to firm size, age, and the host countryrsquo;s level of development.
-
Introduction
There are many alternative views about how a country develops. Some scholars view institutions as the key determinant (North, 1990; La Porta et al., 1998; Acemoglu et al., 2001), while others emphasize human capital (Lucas 1988; Romer 1990; Gennaioli et al., 201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have argued for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 ronment (BE) in which firms operate (World Bank, 2005),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World Bank 1994). Finally, a more recent strand of the literature has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s a source of innovation and, therefore, long-term growth (Glaeser and Gottlieb, 2009; Jones and Romer, 2010; Clarke et al., 2016).
What, however, are the relativ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se alternative, though not necessarily-mutually exclusive, views? And are their effects universal or hinging on the specific context?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is important because governments only have limited
☆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Gilles Duranton, Daniel Lederman, Christine Qiang, Carlos Vegh, and Daniel Xu for comments/discussions on an earlier draft of this paper, as well as participants at Authorsrsquo; workshops for the LCR “Cities and Productivity” Flagship Report that took place in July 2016 and May 2017.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World Bankrsquo;s “Global Research Program on Spatial Development” (P143985), which is funded by UK DFID and the World Bankrsquo;s Multi-Donor Trust Fund, is also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All three authors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World Bank. Corresponding author: L. Colin Xu (lixin.colin.xu@gmail.com); Mail stop: MC 3-307,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lxu1@worldbank.org (L.C. Xu).
https://doi.org/10.1016/j.ceqi.2020.09.001 Received 16 July 2020; Accepted 1 September 2020
Available online 5 January 2021
2666-9331/copy;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ing services by Elsevier B.V. on behalf of KeAi Communications Co. Ltd.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ND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resources with which to deal with key challenges. If there are bottlenecks to a countryrsquo;s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diagnose these to provide a sounder basis for policy (Kremer 1993; Hausman et al., 2005; Li et al., 2011). In this paper, we use firm-level data and city-industry level indicators of the business and agglomeration environment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e above questions have been addressed with cross-country data. However, researchers have recogniz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determinants using cross-country data alone. To see this, consider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institutions or human capital are the key for long term development. The seminal study of Acemoglu et al. (2001) uses settler mortality in early colonial periods as the instrument for current institutions, and, finds that institutions importantly affect current development. However, this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challenged by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营商环境的异质增长效应:全球城市企业层面样本
摘 要
通过利用涵盖128个国家709个城市的企业层面的数据,我们研究了在国家以下一级的营商和制度环境变量的综合列表在解释企业就业和生产率增长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基本的保护(包括腐败)、获得资金和基础设施的机会,以及强大的集聚环境的存在至关重要。相比之下,人力资本和一系列与劳动法规、税收和土地使用权相关的精细商业环境变量并不重要。我们还发现,营商环境的影响因企业规模、年龄和东道国的发展水平而异。
关键词 企业成长;生产率增长;制度;腐败;商业环境;人力资本;集聚
1 引言
关于一个国家如何发展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制度是关键的决定因素(North,1990;La Porta等,1998年;Acemoglu等,2001年),而其他人则强调人力资本(Lucas,1988;罗默,1990;Gennaioli等,2013)。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认为,改善企业运营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世界银行,2005年),包括基础设施(世界银行,1994年)。最后,最近的一些文献表明了集聚经济作为创新来源的重要性,因此对长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Glaeser和Gottlieb, 2009;Jones and Romer,2010年;Clarke等,2016)。
然而,这些尽管不一定相互排斥的替代观点的相对解释力是什么?它们的影响是普遍的还是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政府只有有限的资源来应对关键挑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存在瓶颈,重要的是对这些瓶颈进行诊断,为政策提供更坚实的基础(Kremer,1993;Hausman等,2005年;Li等,2011)。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和城市产业层面的业务和集聚环境指标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问题已经用跨国数据解决了。然而,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仅使用跨国数据很难区分不同的决定因素。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就制度或人力资本是否是长期发展的关键进行辩论。Acemoglu等(2001)的开创性研究使用早期殖民时期的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当前制度的工具,并发现制度对当前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然而,这一解释受到了Glaeser等(2004)的质疑,理由有二。第一,存在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收入的结果变量可以反向导致制度。其次,定居者死亡率作为一种工具缺乏有效性,因为它捕捉了殖民者与土著人口的比率,而这与人力资本相关(在误差项中)。如果我们难以区分人力资本和制度对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又如何区分制度、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对增长的相对影响,更不用说一个国家的营商和集聚环境了。事实上,Gennaioli等(2013)利用全球110个国家的次国家区域数据表明,人力资本在核算区域发展方面往往优于制度。与此相反,Acemoglu和Dell(2010)也使用了次国家区域数据(尽管仅限于美洲)提供了证据,表明制度是次国家差异的关键原因,而这种差异无法用观察到的人力资本来解释。
此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瓶颈”也可能不同。同样,不同类型的公司(即规模和年龄)在约束它们的关键因素上也可能不同。Kremer(1993)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败为例生动地描述了发展瓶颈:它有数万个组件,“由于发射时的温度导致其中一个组件,即o形环失灵而发生爆炸。”事实上,当生产技术在不同的投入或运营环境要素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时,电力供应或政府腐败等瓶颈可能会使其他因素变得不那么有用,进而进一步抑制投资和创新的动力,导致低增长均衡。因此,有必要问一问,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是否面临不同的发展瓶颈?不同类型的公司是否面临独特的瓶颈?
为了克服与跨国数据相关的经验困难,我们遵循Acemoglu和Dell(2010)以及Gennaioli等(2013)的方法,依靠国家间的地方差异。我们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数据作为样本,该样本包含多达80000个企业年的观察结果,覆盖128个不同国家的709个城市。我们使用它来调查在国家内的城市-工业单元的营商环境(BE)的变化是如何与企业就业和生产率增长相关联的。我们关注增长,因为单个企业的增长(以关键投入劳动力和以生产率为代表的质量衡量)是整体国民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而一个企业未能成长的国家不可能会发展。
显然,我们采用了一种广泛的BE类别,阐明了对发展的其他解释。图1显示了我们所检查的BE的类型。第一,《基本发展战略》涵盖了通常被视为发展的基础和根本的方面。它包括政府保护的基本职能,包括遏制腐败和提供基本安全(“政府保护”)。它还包括人力资本的良好供应和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如电力供应和互联网技术),以及获得融资的机会,这被广泛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Levine,1997;demirgu-kunt和Maksimovic,1998;Bloom等,2010)。第二,精细化的BE包括进入和退出的障碍(如获得土地),劳动法规,以及企业的税收环境。集聚环境(AE)的最后一个维度包括企业是否位于大城市(即国家首都或拥有超过100万居民)和“产能集聚”,即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周围都是“有能力”的公司。
WBES公司是随机选择的,它们代表着每个经济体中的非农业私营部门。与纯粹的跨国研究不同,我们的样本规模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可以更自信地解开不同 BE 和 AE 元素在推动企业增长中的作用。与经商(DB)项目不同的是,该项目的指标在法律上是基于少数中型企业(全球范围内的企业规模相同)的答案,而我们的数据集中的营商环境指标实际上是衡量企业实际经验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执法差异很大,事实上的BE措施可能更有助于理解BE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使用微观数据来回答广泛定义的BE如何影响发展的问题是有优势的。首先,通过利用我们数据中存在的BE度量中的城市行业层面的变化,我们可以减轻如果我们选择关注跨国BE变化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在关注城市-行业层面的BE时,我们可以控制国家和行业的固定效应,从而保持由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引起的所有时间不变的国家和行业特定异质性,或行业层面的技术和市场结构差异。因此,我们通过比较国家内城市-工业单元的企业绩效,来确定BE各个维度的影响。最后,我们的样本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从不足500美元到超过24000美元不等。这使我们能够调查各种BE要素的边际影响如何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的实证调查产生了许多新发现。首先,基本的BE(即现代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和政府保护)和集聚环境是企业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我们证明了BE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显著异质性。我们发现,环境效应的影响取决于国家的规模、年龄和发展水平。首先,与大中型企业(LMEs)相比,小型企业往往需要一个更强的基础和精细化的BE。例如,就对就业增长的影响而言,LMEs从劳动力灵活性和企业之间联系(例如获得贸易信贷融资)和聚集方面的良好环境中相对受益更多。此外,当腐败得到遏制时,成熟企业的增长相对更快,而年轻企业则在现代基础设施和精炼BE即,准入门槛、劳动力灵活性)方面表现出更快的增长。另一个新的发现是,一个好的BE的关键要素也因公司所在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异。在低收入国家,获得银行融资和能力集聚对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更为重要。有趣的是,贸易信贷准入只在中低收入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大多数BE要素在促进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被证明是收入水平不变的。
我们的论文与两篇文献有关。第一篇文献研究了制度和营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早期的研究使用较小的样本,并专注于一些特定的因素,如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Clarke等,2015)、产权和腐败(Dollar等,2005;Hallward-Driemeier等,2006;Cai等,2011;Clarke和Xu,2004;Cull和Xu,2005)。最近的一些研究,包括城市经济学文献,调查了集聚环境的各个方面——即本文所述的能力集聚,或企业所在城市的规模和/或密度——对创造就业机会的影响(Clarke 等,2016 年)或特定国家内的地方生产力水平(Combes和Gobillon,2015 )。第二个相关文献使用了次国家区域数据来阐明经济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Acemoglu和Dell(2010)表明,机构可能是美洲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关键原因,而这种差距无法用观察到的人力资本差异来解释。Gennaioli等(2013)提供的证据表明,人力资本在核算地方发展和企业绩效差异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我们与上述文献有几个方面的不同。关于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制度的重要性(Acemoglu等,2001)、金融(Levine,1997;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人力资本与制度的相对重要性(Glaeser等,2004;Acemoglu和Dell,2010,Gennaioli等,2013),以及金融与产权的相对重要性(Johnson等,2002;Cull和Xu,2005)。通过在单个数据集中控制这些因素——我们可能在单个研究中拥有最全面的关键BE和集聚环境列表——并通过控制国家和行业的固定效应,我们能够更好地减少潜在的遗漏变量偏差,并且因此,更令人信服地确定了不同BE要素对公司绩效的相对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融资和基础设施可能比制度和人力资本更重要,因此必须考虑集聚环境。此外,企业特征和国家发展状况对企业和集聚环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据我们所知,我们的论文是第一篇允许BE效应因收入类别而异的论文。
2 数据和方法
主要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对128个国家709个城市的企业调查(WBES)。收集WBES数据是为了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进行基准测试,并了解公司业绩的决定因素。样本中最富裕的国家是瑞典,人均GDP为4.6万美元,最贫穷的国家(如布隆迪、利比里亚、马拉维、埃塞俄比亚)人均GDP约为200美元。国家人口从圣基茨和尼维斯的5.2万到中国的13亿不等。在每个国家,调查都是基于从国家统计局获得的符合条件的公司范围,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置换,结果是该国非农业私营经济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分层是基于两个标准:行业活动和公司规模。通常,分层抽样的结果是每个国家100至1000家公司,中型城市有108家公司。工业范围从制造业、建筑业到服务业、零售和批发贸易。每个调查主要是一个横断面数据集。然而,公司会被问及调查年度和调查前三年的销售和就业情况,这使我们能够构建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化增长率。我们包括2006年以后收集的数据,尽管有些WBES是在更早的时候进行的。在2006年之前,各国在问卷格式、涵盖的部门和抽样方法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此外,2006年以前的调查样本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完整的变量和数据源列表如表1所示;我们的关键变量的汇总统计数据在表A1中。我们的最终样本包括128个国家709个城市的约80000家公司。
2.1 经验规范和评估策略
我们关注增长,包括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两个原因。首先,单个企业的增长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来源,而一个企业无法增长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的。其次,关注企业增长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确定BE对增长的贡献。静态绩效指标,如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比企业增长指标更容易受到持续性测量误差源的影响,并受企业特定市场力量的影响。通过使用企业增长和静态企业绩效的差异,我们基本上过滤掉了时不变的测量误差。我们的基本估计方程是:
在这里,i、k、c、j和t分别代表公司、国家、城市、行业和年份。添加时间下标是因为不同国家在不同年份进行调查,而不是由于面板元素。我们研究了两个不同的结果变量(),即公司的就业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其中劳动生产率是用销售额除以员工数量来衡量的,以不变美元表示。理想情况下,我们也应该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缺乏资本和物质信息的信息使我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由于增长率受到异常值问题的严重影响,我们遵循Davis和Haltiwanger(1999)的方法,在开始和结束年份,通过将调查年度和三年前的就业(或劳动生产率)变化除以就业的简单平均值来计算中点增长率(或劳动生产率)。这将导致的增长率限制在-2到 2之间,从而大大减少了异常值的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FIRM是一个企业层面的控制向量,包括外资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企业规模和年龄的虚拟变量。这些虚拟变量的一个功能是根据可观察到的特征帮助控制跨城市的公司分类——具有有利于快速增长的特征的公司可能系统地分类到例如大城市的可能性。稍后我们将讨论排序的可能性。是城市工业层面潜在商业效率的一个向量。虽然企业层面的BE指标可以从WBES获得,但我们并不直接使用个体的答案,因为它们反映了企业做出的选择,因此是内生的。相反,我们遵循文献,通过使用城市行业层面的 BE 指标的当地平均跨公司作为当地BE的代表来(Dollar等,2005;Hallward-Dreimeier等,2006;Aterido等,2011;Xu,2011)。我们总共使用了大约4500个独特的城市工业单元。为了遵循惯例(Moulton,1990),我们在关键聚合变量级别(即城市-行业)对异方差校正错误进行聚类。
对于局部BE的某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客观衡量标准,研究人员依赖于主观评估。通常,调查的问题是:“XX(即特定BE领域的通用名称)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公司的发展?”答案从0缩放到4,数字越大意味着约束越严格。为了帮助解释,对于每个障碍问题,我们为该区域构造中等或严重障碍的虚拟变量(即3和4的值),称其为XX障碍。然后我们计算出XX障碍的城市平均水平,并将其作为XX方面的本地BE指标。
一个相关的担忧是,具有良好的不可观察特征(比如产能)的公司可能会被分到大城市。为了检验其有效性,我们使用企业对高科技产业的隶属度作为企业质量或技术的代表,并查看位于大城市的企业是否更有可能从事高科技产业(即金属和机械、 电子、化工和制药、非金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8896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