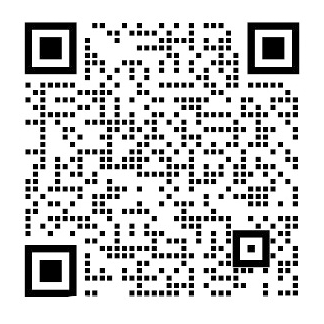迈向21世纪外交政策的影响理论:全球化世界中的公共外交
亚历克斯·埃文斯和大卫·史蒂文
介绍
看看当今最大的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流行病、能源安全、恐怖主义和全球化的其他'影子面'——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发现最难应对的挑战非常分散,涉及和数百万(如果不是数十亿)人的信仰。1
以气候变化为例。在这种情况下,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在于无数企业和个人做出的支出、投资和行为决策。以艾滋病毒/艾滋病为例,长期前景取决于各国在影响可以想象到的最个人问题——其公民的性行为——方面的成功程度。或者想想发展中国家善政的挑战,正是政治文化的性质——以及组织和法律——就产生了不同。
随着问题日益分散,政府的工作方式也不得不改变。外交官们正在走出一个舒适区,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同龄人身上。随着'人民之间的战争'超越旧的国家间冲突模式,士兵面临着武力的局限性。3 发展专家面临的事实是,在脆弱状态下,不能简单地通过大量资源转移来'购买'开发。4 在所有三个领域,人们重新关注文化;对思想和价值观的力量;以及等级组织与非正式网络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是,对于在全球化世界中,政府要考虑的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发挥它?各国如何整合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所有方面?他们如何为追求共同目标而激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松散联盟?这些问题是当今公共外交的核心。
三种公共外交挑战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了解目前主导国际议程的全球问题的性质。三种挑战可以用来说明挑战的广度:第一,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构成的威胁——毫无疑问,将来是其继任者;第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效的国家;第三,前所未有的风险构成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些都是不同的问题类别。基地组织的全球圣战是破坏并最终取代当前世界秩序核心的机构的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不善会把他们拖入混乱——在最坏的情况下,向邻国和其他地区输出混乱。外部干预旨在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其发展陷阱,其动机是自身利益。稳定的气候是全球的公益事业。尽管世界一些地区(主要是较贫穷的地区)将因气候条件变得更加恶劣而遭受不成比例的苦难,但底线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每个人都享受着稳定气候的果实,或者没有人享受。因此,变化需要向各个方向流动,包括跨越国家,在各州内部。
综上所述,三合会是影响新议程需要解决的问题类型的代表性样本。那么,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新的公共外交呢?
恐怖主义作为公共外交
让我们从恐怖主义开始。现代恐怖运动旨在探讨社会,以发现和利用其生理和心理弱点。他们使用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叙事来激励他们的支持者采取行动。在压力之下,它们采用分散的组织结构,并寻求发展其他权力来源。他们是创新的传播者,把言行的宣传编织在一起,挖掘新的沟通渠道的潜力。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们依靠煽动东道国社会作出不利反应。预计国家将承担破坏自身合法性的大部分责任。5
以基地组织为先锋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运动很好地吸取了这些教训。基地组织的目标是成为大卫·基尔库伦所称的'世界革命的控股公司和清算所'。6乌萨马·本·拉丹在1994年宣布圣战时,试图将一系列地方不满地束缚成一个单一的压迫叙述。穆斯林面临着一个犹太-基督教联盟,认为他们的'血液是最廉价的,他们的财产和财富只是掠夺'。7 基地组织已经从一个中央组织逐渐退化为无定形网络,它制定了一个简单的战略。8 将'笨重的美国大象'卷入海外冲突,从而激化潜在的新兵,并制造一种暴力循环,目的是'让美国流血到破产的点'。9,本·拉登引用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英国外交官的话来支持他的说法 ,即'我们和白宫似乎同在一个小组向美国自己的目标开枪'。10
本·拉登是典型的公共外交官,尤其是他过去政府讲话的方式。在2004年西班牙大选后(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在马德里爆炸事件中被击败)之后,他在对'欧洲人民'的讲话中说:针对事件和民意调查显示,欧洲大多数人希望和平的积极举措,我呼吁只有男人,特别是学者、媒体和商人,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提出欧洲人认识到我们的事业的正义,特别是苍白的,充分利用媒体的巨大潜力。
基地组织的信息也被分割了。暴力图像在使潜在支持者(青年)激进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互联网为无中介通信的点对点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12 穆斯林社会中的传统权威来源受到破坏,被斥为'邪恶学者、腐败的宫廷部长、雇佣作家等'。13 向非穆斯林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如果不通格的话,就是一个:'通往安全的道路从停止敌对行动开始'。西方国家的公民必须说服他们的政府,才能接受基地组织的要求,才能看到和平。
在基地组织中,我们看到一个少数人试图实现其世界观的普遍化的例子。因此,晋升至关重要。其通讯经过精心抛光、品牌和展示,甚至塔利班——曾经粗心大意的形象——也派他们前往伊拉克,接受基地组织视频制作部门的现代通信技术培训。14 更重要的是,它的行动本身是为了达到影响力而精心策划的。正如大卫·基尔库伦所警告的:当心脚本的敌人,谁扮演全球观众,并试图击败你在全球公众舆论的法院。15
发展作为公共外交
第二,让我们考虑在许多发展中的合作社中改善治理的必要性。一方面,'发展国家'是减贫成功的基石——正如许多亚洲国家所表明的那样。另一方面,当脆弱国家崩溃时,由此产生的真空不仅威胁着本国公民,也威胁到本国国家,同时也为有组织犯罪或恐怖主义提供了避风港,成为不受管理的移民的引擎。正如罗伯特·库珀所说,'我们可能对混乱不感兴趣,但混乱对我们感兴趣。16
如果有效国家是理想的目的地,我们缺乏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表明如何达到目标——最近关于伊拉克冲突后重建的激烈辩论以及肯尼亚的暴力和内乱就证明了这一点。 2008年欧洲捐助者支持的治理工作往往相对技术性,侧重于政府行政部门,并面向公共服务改革或预算进程等领域。任何政治上的东西通常被认为太冒险了,不能被卷入其中。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发展了'转型外交'的论调,但在实践中,美国尚未具体说明这种做法的含义。显而易见的是,在促进有效国家的挑战中,很大一部分是影响力,而只是部分地与支付资金有关。事实上,鉴于援助支出可能支持根深蒂固的腐败和庇护制度(肯尼亚的情况显然如此),可以说,除非援助捐助者拥有适当的机制,否则资金更容易影响治理。到位的'首先不伤害'。
在发展联合尝试中,一个更复杂的影响理论可能支持善政,寻求影响脆弱国家治理的国际行为者需要双重需要:第一,明确说明它们能发挥多大影响力;第二,明确限制它们应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对前者的评估需要从现实意义上开始,即外部玩家希望对作为客人的国家产生多大影响。蒂普·奥尼尔有句名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这和其他地方一样适用于发展算利。18 国际行动者充其量只能在边缘施加影响,通常只有在他们准备共同行动时才能施加影响。他们很少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只要能够,它很容易改变,因为情况会变坏,坏情况也会变好。
关于后一点,国际行动者需要更清楚地了解主权,以及他们将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如果外部国家被认为在内政上处于,它们就有可能受到强有力的回击。在这些情况下,意外的公共外交削弱了官方政策目标,而且有许多情况。美国在巴基斯坦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巴基斯坦人认为巴基斯坦应该在反恐战争中与美国合作,而近半数只有18人。几个月前。19同恐怖主义一样,这里的关键需要是让国际行动者首先了解它们所处的环境:谁有影响,哪些想法和叙述具有牵引力,以及它们希望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
气候作为公共外交的气象
气候变化对我们的集体安全构成比脆弱国家更大的危险。面对如此规模和难度如此空前的问题,世界迄今对这一问题有了集体理解,这是值得注意的。这证明了一些非传统外交的有力例子的有效性。
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例,这是一个将非治理者—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制度化的机制。它在为国际社会参与这一问题建立一个审议平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反过来,气候变化经济学又有助于将经济和环境叙事结合起来,形成关于行动和无所作为各自代价的辩论。它与戈尔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一起,为国际社会开始就新的气候协议进行谈判创造了政治空间。
与此同时,已作出相当大的努力,破坏正在形成的反对紧急行动的共识,在布什总统拒绝《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已加强这种共识。新参与者被带到了辩论中,特别注重激励信仰、科学和商业界,并将注意力转向州和市一级的政治结构。英国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达成的气候'协议'是这项工作的缩影,托尼·布莱尔和阿诺德·施瓦辛格在一群高级商界领袖的看着下,摆出姿势拍照。
在巴厘气候首脑会议之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现在,焦点正在从相对解决的'问题辩论'转向'解决方案辩论',这场辩论仍然不成熟和混乱。20 一个新的'游戏'即将开始,一个与国际象棋相反的动态游戏。随着朝着最终结局迈出的每一步,董事会棋子的数量将会增加,而不是缩减。随着各种派别突然出现,并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这种温暖行为将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激起了人们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充满激情的尝试。
游戏也是不对称的,交易撮合者需要'赢'(在国际上达成交易,在国内立法等),而交易破坏者只需要阻止他们(僵局适合他们)。如果政府允许自己把太多精力放在谈判的'泡沫'上,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致力于达成全球协议的各国政府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数十个国家(如果不是没有抗议的话)中影响不断演变的辩论,同时利用国内政策来表明它们的承诺力度。成功取决于建立联盟,并让他们专注于大局,无论是我们面临的集体危险的程度,还是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机会。
公共外交挑战
那么,在三大全球挑战中,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共同点呢?
最根本的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当决策者处理21世纪的主要全球问题时,他们——从延伸和定义上讲——从事公共外交。理解、参与和影响非国家行为者的能力是上述所有三个问题取得进展的核心。
第二,在理解问题和描述解决办法时,要注意根本的困难。在诸如气候变化、分裂主义或恐怖主义等多方面问题上,没有一个机构、政府或专业领域能够全面了解情况。因此,未来公共外交官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他们如何综合信息,以及如何与盟友分享信息。例如,在帕基斯坦,国际资助的民意调查为衡量2008年2月大选前民意异常变化提供了衡量标准。这种资源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开源的知识库,帮助支持该国脆弱的民主。
第三,如果'联合性'和统一的集体行动的挑战强烈适用于信息收集,那么在考虑实际施加影响时,情况就加倍了。在这里,任何一个政府(或机构或个人)能够独立实现多少,也是真正的限制。事实上,自9/11以来,西方在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的团结方面一直非常差劲,其'品牌'在国内外都遭遇了惨败。相反,正如基地组织所表明的,关键是在包括政府、媒体、民间社会团体和许多其他组织在内的联盟中工作。
第四,应该清楚,内容的质量是一切有效的公众化。只有令人信服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展望才能使网络长期活跃。那么,我们的故事比对方讲述的故事更强大吗?这就是为什么抓住主动权,不断强调大局是那么的无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它本身就是一个联盟——利用先发制人减排的提议,试图迫使达成新的全球协议。但欧洲的做法也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故事。欧洲各国政府尚未开始表现得像他们期望达成协议所需的快速而大幅度的削减。这造成了不确定性,削弱了他们需要建立的联盟,削弱了他们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21
公众浸渍的目标
所有这些都使公共外交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它的使命似乎从未如此重要。各国政府在不再垄断的国际领域面临一系列庞大而复杂的挑战。当然,国与国外交仍然非常重要,但它只包含一些答案——特别是当政府发现它们的权力正在向国际层面转移,向下转向非国家行为者时。
但是,关于公共外交的困惑和它能做什么,是比比皆是。一次又一次,政府被引诱到一些诡异的企图中去美化他们国家的形象,好像一个肤浅的、短暂的营销活动可能会改变一个民族品牌的构造板块。或者,他们试图兜风,否则不受欢迎的政策,徒劳的希望,行动不再比语言更响亮。公共外交很少在战略上使用。各国政府很少将其所有行动、言论和资源与它们希望实现的影响保持一致。
因此,在全球化世界中,公共外交应设定什么样的目标(见图1):
|
共享操作系统 |
集体应对共同问题的框架 |
|
共享平台 |
竞选集体愿景或首选解决方案的州和非国家行为者网络 |
|
共享意识 |
对联盟可以团结在一起的问题的共同理解 |
图1:新公共外交的目标
首先,公共外交是建立共同意识——对一个联盟可以团结在一起的问题的共同理解。这里的任务不是简单地积累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存在丰富,而是投资于分析、综合和传播。状态参与者和非状态参与者使用相同的数据吗?已经出现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吗?是否有讨论和辩论的中心?
共享意识应该是共享平台发展的前奏。新的公共外交通常——也许总是——是一项多边追求。目标是围绕共同的愿景或一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Towards a theory of influence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policy: public diplomacy in a globalised world
Introduction
Look at todayrsquo;s biggest global issues – climate change, pandemics, energy security, terrorism and other lsquo;shadow sidesrsquo; of globalization – and itrsquo;s striking that the challenges governments find it hardest to deal with are highly diffuse, involving the actions and beliefs of millions (if not billions) of people.1
Take climate chang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is case is about the spending, investment and behavioural decisions made by countless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Consider HIV/AIDS, where the long-term outlook depends on how successful states are at influencing the most personal issue imaginable: their citizensrsquo; sexual behaviour. Or think of the challenge of good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 as much as organizations and laws –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As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stributed, the way governments work is having to change too.2 Diplomats are breaking out of a comfort zone within which they have focused much of their energy on talking to their peers. Soldiers are confronting the limitations of force as lsquo;war amongst the peoplersquo; overtakes the old paradigm of interstate conflict.3 Development specialists are facing the fact that, in fragile states, development cannot simply be lsquo;boughtrsquo; through large transfers of resources.4 In all three fields, there is a renewed focus on culture; on the power of ideas and values; and 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and informal networks.
But there are still hard questions for governments to consider about their role in a globalized world. What influence do they have? How can they best exert it? How do countries integrate all aspects of their hard and soft power? And how can they animate loose coalitions of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in pursuit of a common goal? It is these questions that lie at the heart of todayrsquo;s public diplomacy.
Three types of public diplomacy challenge
In thinking about these questions,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global issues that now dominate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Three can b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breadth of the challenge: first, the threat posed by Al-Qaeda, its affiliates – and in the future, no doubt, its successors; second, the need for effective stat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ird, the unprecedented risk posed by climate change.
These are different classes of problem. Al-Qaedarsquo;s global jihad represents a targeted attempt to undermine, and ultimately replace, the institutions at the heart of the current world order. The intended direction of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K, is inbound.
Poor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drag them into chaos – in a worst-case scenario, exporting disorder to neighbours and beyond. Outside intervention aims to help these countries escape from their development traps, and is motivated by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Here, the desired direction of change (agai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UK) is outbound.
A stable climate is a global public good. Although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mostly the poorer ones) will suffer disproportionately as climatic conditions become more hostile, the bottom line is a simple choice: everyone enjoys the fruits of a stable climate, or no one does. Thus change needs to flow in all directions, both across states and within them.
Taken together, then, this triad is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type of problem a new agenda for influence will need to tackle. So what can they tell us about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Terrorism as public diplomacy
Let us start with terrorism. Modern terror movements are designed to probe societies to find and exploit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aknesses. They use powerful ideologies and narratives to motivate their supporters to act. Under pressure, they adopt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seek to develop alternative sources of authority. And they are innovative communicators, weaving together the propaganda of word and deed, and exploiting the potential of new communication channels.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they rely on provoking their host societies into an adverse response. The state is expected to carry most of the burden of undermining its own legitimacy.5
The Islamist terrorist movement, with Al-Qaeda as its vanguard, has learned these lessons well. Al-Qaedarsquo;s aim is to become what David Kilcullen calls lsquo;a holding company and clearing house for world revolutionrsquo;.6 In his 1994 declaration of jihad, Osama bin Laden attempted to yoke a series of local grievances into a single narrative of oppression. Muslims are confronted by a Judeo-Christian alliance that believes their lsquo;blood is the cheapest and that their property and wealth is merely lootrsquo;.7 Al-Qaeda, which has steadily degraded from a 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to an amorphous network, has set out a simple strategy.8 Entangle lsquo;the ponderous American elephantrsquo; in conflict overseas, thus radicalizing potential recruits, and creating a cycle of violence that aims to lsquo;make America bleed to the point of bankruptcyrsquo;.9 Mischievously, bin Laden quotes an unnamed British diplomat speaking at Chatham House to support his assertion that lsquo;it seems as if we and the White House are on the same team shooting at the United Statesrsquo; own goalrsquo;.10
Bin Laden is the quintessential public diplomat, not least in how he speaks past governments. In an address to the lsquo;peoples of Europersquo; after the 2004 Spanish election (when Joseacute; Mariacute;a Aznar was defeated in the wake of the Madrid bomb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402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