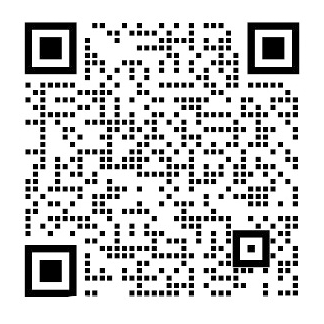语言和文化身份:
---平衡马来西亚的国家和国际需求
原文作者:Saran Kaur Gill单位: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摘要:世纪之交,许多亚洲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下语言政策转变带来的紧张局势。通常情况下,这些压力是由于从国家语言的领域的转变而产生的,从不同程度的教育体系中国家语言到英语的建立,从小学到高等教育。这种日益增加的英语霸权引起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这个复杂的情况下,Tsui[1]和Tollefson[2](2007)在他们的书《亚洲语境中的语言政策、文化和身份》中恰当地提醒我们,“语言政策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这需要有系统的理由来阐明两种相互作用的力量之间的对立,或国家和国际需要的因素。”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必须阐明对立的力量,以了解语言政策变化的动态,以及决定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
我们将从回顾历史开始——对过去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情况并根据得到的反应做出决定。
关键词:民族语言 文化认同 教学媒介 发展方向
一、马来西亚独立后历史上的语言问题
马来西亚,由于历史的迫切需要,是一个后殖民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人口,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复杂性。马来西亚不仅有一种语言,而且有许多重要的语言,主要是由于其多民族人口的移民血统。在一背景下,对马来西亚独立前后和独立时期的语言政策决策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时期植根于传统的民族主义。在选择和建立民族语言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有必要实施一种国家需要的单一语言政策的传统民族主义方法?
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的选择及制度
在马来西亚于1957年从英国独立出来之后,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马来社区,被以下问题所困扰:“国家的主人是谁?”“什么是国家认同的象征?”“这个国家的历史意义是什么?“”(Crouch[3], 1996: 155)在独立前的历史时期,马来人感到不安,并受到移民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的威胁。(Crouch, 1996: 157)
这些潜在的边缘化的感觉加上强制的帝国主义,导致了土著民族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被恢复到荣誉的地方”的迫切需要。(爱默生,1960:152)他们通过语言、宗教和国歌等象征性的类别加强了合法化,这成为了非常强烈的认同迹象。其他民族对这些符号的承认和接受,为统治集团提供了一种集体价值和合法性的感觉。这就是霍洛维茨在他关于种族群体冲突的广泛讨论中所提到的——群体,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通过政治统治建立“相对集团价值”和“相对群体合法性”,以及民族权利政治的高象征内容。
因此,在此期间,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性主张,把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和官方语言,即教育和行政语言。毕竟,建立一种民族语言是“民族主义最强大的象征性载体。”(Coulmas[4],1988:前言) 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一种国家的语言不仅需要这个国家的主导群体确认其合法性同时也是一种统一全国多民族公民的工具,以在国家层面上提供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二、高等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
在高等教育背景下,高校在培养和发展国家高层次人才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高等学校的文化与教育语言的选择和实施有着密切的联系。马来语是所选的民族语言,有一个既定的农业和文学背景。因此,为了使语言能够成为教育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它必须现代化,并配备专门的术语和结构,特别是科学和技术学科。对于马来西亚语来说,作为一种知识语言而被认真对待并获得教育资本,它需要现代化,必须鼓励学者将专门知识写或翻译成马来语。因此,在30年的时间内,马来西亚为激活官方语言状态和语料库计划注入了巨大的努力和资源。
如何将英语地方化?
从英语到马来语的转变是在1969年,以学校开始的主要教学媒介,并在1983年达到了大学水平。英语的角色后来变成了第一种第二语言——在学校教学中,它成为了一门必修课程,但在学校系统中却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接受的。
从英语到马来语的语言政策的变化跨越了独立后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期。我们现在转向90年代:这一时期再次出现了对语言政策进行修改的信号,并在2002年达到顶峰,将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英语转换为教育语言。
三、21世纪:教学媒介变革的原因
政治领导:变革的背景。
这一变化有很多原因(在吉尔(2005)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但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其中一个。从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的采访开始,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是一个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语言政策和计划,以对知识经济的需求做出回应。
马哈蒂尔被问到:“关于最近MOI在学校的变化,现在已经影响了高等教育,原因是什么?科学和数学领域将为这一变化的语言政策提供怎样的动力?”
我们的教育系统和其他教育系统一样,其目的是让我们获得知识。如果我们掌握了国家语言的知识,那就继续吧。但事实是,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篇关于新研究的论文发表,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是用英语写的,要把英语翻译成马来语,需要一个会3种技能的人。这门课的两种语言都需要翻译但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有能力和愿意去做这件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学英语的学生可以更直接、更容易的接触到英语中所有的知识。
阐明影响语言政策变化的因素。
这就导致了这一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需要用英语来获取科学和技术,这也增加了在马来语中翻译和本土文字的挑战。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迄今为止所有的努力都不足以让这个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获得信息和知识?
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关键信息获取:马来语的出版物翻译缓慢
Shaharir[5]是一位知名的数学教授,他详细解释了在马来语出版物的出版缓慢的各种原因。这些内容包括在学术推广计划中缺乏对马来语出版物的认可度,以及冗长的出版过程,这使学术作家们的努力受挫。(Shaharir,2001:107 - 2001)。
翻译过程以缓慢的速度进行,这使情况更加复杂。根据国家翻译机构(ITNM)的执行主任Hj. Hamidah Baba[6]所说,全职翻译每天只能翻译5-8页,而兼职翻译每天足底多可以翻译3页。
这些原因伴随着英语知识爆炸,具体可描述为世界上有超过10万的科学期刊,并且这个数字正在以每天5000篇的速度增加,增加了3000万的现存数量。(Bilan in Martel[7], 2001: 51)描述了在获取英语知识和信息方面,将越来越充满挑战的形势。
在讨论语言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时,重要的是要了解在实施过程中,关键角色参与者、讲师和教师对这种改变的态度和反应。
关键人物:对教学媒介变化的看法
来自9所公立大学的670名讲师参与了这项研究,来自8所公立大学的大部分讲师(70.2%)同意按照政府和国家的要求改变教学媒介。
我们现在先来研究马来西亚Kebangsaan [8]大学(UKM)的讲师的反应。
与其他8所公立大学的大多数讲师的回答不同,在UKM的大多数人不同意教学的媒介的变化(70.5%的被调查者),只有少数人同意(29.5%的受访者)。要了解该调查结果的原因,就必须了解UKM的历史。
马来西亚Kebangsaan大学是第一所仅用马来语作为教育媒介的大学,这所大学比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都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将马来语的使用、发展和现代化作为一种知识和教育的语言。这所大学的使命宣言是“mendaulatkan Bahasa Melayu[9]”。《使命宣言》的语义学分析揭示了马来知识分子所持的民族主义力量。与马来语有关的动词是mendaulatkan,“to ennoble”,这个动词通常只与皇室有关。在马来文化中,在国家里,国王的地位是最高的。因此,动词mendaulatkan已经被用来重新定义和强调语言的神圣性,这体现了马来知识分子对语言和大学使命的强烈感受。
Smolicz[10]解释了所有团体对试图改变代表其文化认同核心元素的语言的立场的强烈反应。他说:“当人们觉得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文化中最重要、最显著的元素有直接联系时,有关元素就成为了这个群体的核心价值。任何试图改变其传统文化的尝试,都会被提出反措施,以帮助该组织确定其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并因此而为他们的辩护作出一切努力。”(Smolicz,1981:1981)
四、国家未来的挑战:平衡国家的发展与民族语言文化认同的维系。
在那些对语言政策变化感到沮丧的演讲者中,人们对我们民族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潜在侵蚀非常关注。人们担心,国家将发展出一代放弃自己的文化遗产、追求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公民。这也同样是Tsui和Tollefson(2004: 7)所表达过的提醒,在英语教学中,“可能会产生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矛盾的国民,以及那些被剥夺了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因此,许多国家面临着必须在民族语言和日益扩大的英语传播及功能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
这些担忧合理吗?把我们的教育边界开放给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意味着我们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并且会允许帝国文化摧毁我们的民族和民族特性吗?
其他国家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Tsui和Tollefson(2007: 9)通过描述其他国家如何“通过英语来重建国家文化认同”来解决这个悖论。他们通过描述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来解释这种重建,在此,我将重点放在马来西亚方面。
在马来西亚的背景下,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挑战的产生,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建需要通过英语来发展。那些仍然对语言转变的现状表示不满的学者们,需要意识到这种心态的变化,并意识到当前民族主义观念所需要的改变。这位前总理为这种语言的改变提供了动力,提醒我们民族主义的整个概念需要重新定义。Tun Mahathir强调,“我们需要从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转变为一种语言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民族主义和以发展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成功,能够昂首挺胸,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而不是成为那些贫穷又落后的没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做着别人的仆人。如果我们没有知识,我们就会成为那些有知识的人的仆人。”(2005年6月16日)
很明显,传递的信息是通过英语重建民族主义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需求——从语言民族主义到知识驱动的民族主义、发展导向的民族主义,这是整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面对我们国家面临的这些看似矛盾的挑战,当务之急应该是什么?在我们关注和致力于通过马来语来维护和维持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讲师们正面临着教学媒介的转变的挑战,这给学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要求。这对于那些属于“语言过渡一代”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在马来语中受过教育,在马来语中授课和教学,现在正在转换为英语,并有望在英语教学中有效地发挥和发挥作用。
在教学和学习领域,语言的掌握是重要的,能够运用它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思想是很重要的。但要获得高水平的能力需要时间,因此,在过渡时期应该做些什么呢?
为此,最好将欧洲经验转化为我们在语言变革的过渡时期为帮助语言过渡而采取的方向。
威尔金森描述了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沟通挑战的本质,他说,“通过一门外语学习知识,不仅仅意味着改变教学语言,它还包括有意识地设计整合内容和语言目标的课程。hellip;这是因为,仅仅通过一种外语提供方案而不设定使用与内容相关的语言的性能指标,就会使方案和机构的质量和声誉受到威胁。”(威尔金森,2004:10)
我们需要考虑并为我们的学术工作人员提供帮助的问题,是在一个新媒体中面临着加强教学和学习的挑战,这是欧盟委员会教育和文化总干事提出的。他在欧洲高等教育背景下阐述了这些观点,但这些观点在马来西亚的背景下是相关的,他说,“我们怎样才能确保通过外语教学的工作人员在语言方面有足够的交际能力,并在CLIL3技能和其他学科方面进行专业培训?
我们如何确保学术人员在设定学习目标和评估CLIL[11]环境(与标准学习环境完全不同)的学习成果方面有足够的培训?
简而言之,大学如何确保通过一门额外语言教学的人员真的在整合内容和语言?200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Balanc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ed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Saran Kaur Gilll
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INTRODUC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many Asian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tensions arising from the linguistic shift in language policies stemming from pressures of globalization. Very often, these pressures arise as a result of the shift in domain use from tha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at varying level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ranging from the primary to higher education. This increasing hegemony of English elicits reactions of varying degrees of anxiety over its impact on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is complex situation, Tsui and Tollefson (2007: 17amp;19) in their book, “Language polic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Asian Contexts” appropriately remind u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s dialectical.” It requires systematic reasoning to unravel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wo interacting forces or elements of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eds of the nation.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t will be essential to unravel the opposing force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chang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how the decisions impact on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ies.
We will begin by going back to history – an appreciation of the past always helps us understand responses and reactions to decisions made in the present.
LANGUAGE CONCERNS IN PRE AND IMMEDIATE POST-INDEPENDENCE HISTORY OF MALAYSIA
Malaysia, due to the exigencies of history, is a post-colonial nation with a diverse ethnic population possessing great social and cultural complexity. Malaysia has not just one but many significant languages, largely as a result of the immigrant ancestry of its multi-ethnic population. In this context, it is essential to examine the language policy decisions made in Malaysia in the pre and immediate post-independence period, a period rooted in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What wer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of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as it went about selecting and institut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Why was there a need to implement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approach of a one-nation one-language policy for national needs?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 and the Selection and Institution of Bahasa Melayu as the National and Official Language
After the British had given independence to Malaya in 1957,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the Malay community, was plagued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o are the owners of the country? What are the symbols of national identity?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nationrsquo;s history?” (Crouch, 1996: 155) The Malays during the pre-independence period of history felt insecure and threatened by the numerical and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cited in Crouch, 1996: 157)
These feelings of potential marginalisation coupled with enforced imperialism resulted in an acute need amongst the indigenous ethnic group for “their own cultures and histories be restored to a place of honour.” (Emerson, 1960: 152) They reinforced legitimization through symbolic categories like language, religion and the national anthem, which became very strong signs of identification.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se symbols by other ethnic groups provided the dominant group with a feeling of collective worth and legitimacy. This was what Horowitz in his extensive discussion of ethnic group conflicts refers to as the need for groups, and especially dominant ethnic groups, to establish “relative group worth” and “relative group legitimacy” through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the high symbolic content of politics of ethnic entitlement. (1985: 185)
Therefore, one of the strong symbolic claims that was asserted during this period was that of the institution of Bahasa Malaysia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official language - 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fter all,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most powerful symbolic vehicle of nationalism.” (Coulmas, 1988: Preface) There was a strong feeling that a national language was needed not only to affirm their legitimacy as the dominant group in this country but also as a tool to unify the multi-ethnic citizenry of the nation – to provide a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LANGUAGE POLICY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DOMAI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context, universities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intellectualizing and developing the higher-order human resource of a nation. The culture of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s strongly intertwined with the 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Bahasa Malaysia, the selected national language, had an established agrarian and literary background. Therefore, to enable the language to function as a major player in the domain of education, it had to be modernized and equipped with terminology and structures for particularl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iplines. For Bahasa Malaysia to be taken seriously as an intellectual language and to gain educational capital, it needed to be modernized and scholars had to be encouraged to write or translate specialized knowledge into the language. Thus, tremendous efforts and huge resources were injected for activating both status and corpus planning for over a period of 30 years.
Where then did this place English?
The transition from English to Bahasa Malaysia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began in 1969 in schools and reached university level in 1983. The role of English then became that of the first second language – from being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schools, it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80318],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