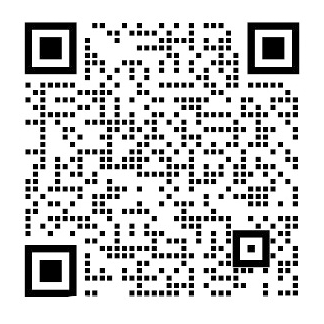文献翻译
出处:Kressamp;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 2006:p18-37
原文:
The semiotic landscape: language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schooling, children are constantly encouraged to produce images, and to illustrate their written work. Teachers comment on these illustrations as much as they do on the written part of the text, though perhaps not quite in the same vein: unlike writing, illustrations are not lsquo;correctedrsquo; nor subjected to detailed criticism (lsquo;this needs more workrsquo;,lsquo;not clearrsquo;, lsquo;spelling!rsquo;, lsquo;poor expressionrsquo;, and so on). They are seen as self-expression, rather than as communication – as something which the children can do already, spontaneously, rather than as something they have to be taught.
By the time children are beyond their first two years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llustrations have largely disappeared from their own work. From here on, in a somewhat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 writing increases in importance and frequency and images become specialized. This is made more problematic by the facts of the present period, in which writing and image are in an increasingly unstable relation. We might characterize the situation of say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in this way: texts produced for the early years of schooling were richly illustrated, but towards the later years of primary school images began to give way to a greater and greater proportion of written text. In as much as images continued, they had become representations with a technical function, maps, diagrams or photographs illustrating a particular landform or estuary or settlement type in a geography textbook, for instance. Thus childrenrsquo;s own production of images was channelled in the direction of specialization – away from lsquo;expressionrsquo; and towards technicality. In other words, images did not disappear, but they became specialized in their function.
In many ways the situation in school remains much the same, with two profoundly important provisos. On the one hand all school subjects now make much more use of images, particularly so in the years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many of these subjects, certainly in the more technical/scientific subjects such as (in England) Sci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r Geography, images have become the major means of representing curricular content. In the more humanistic subjects – for example, History, English and Religious Studies – images vary in their function between illustration, decoration and information. This trend continues, and it is the case for worksheets, in textbooks and in CDROM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no teaching or lsquo;instructionrsquo; in the (new) role of images (though in England, in the school subje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re is teaching in desktop publishing). Most importantly, assessment continues to be based on writing as the major mode. Students are called upon to make drawings in Science, Geography and History; but, as before, these drawings tend not to be the subject of the teacherrsquo;s attention, judging by their (written) comments on the childrenrsquo;s work. In other words, materials provided for children make intense representational use of images; in materials demanded from children – in various forms of assessment particularly – writing remains the expected and dominant mode.
Outside school, however, images play an ever-increasing role, and not just in texts for children. Whether in the print or electronic media, whether in newspapers, magazines, CDROMs or websites, whether as public relations materials, advertisements or as informational materials of all kinds, most texts now involve a complex interplay of written text, images and other graphic or sound elements, designed as coherent (often at the first level visual rather than verbal) entities by means of layout. But the skill of producing multimodal texts of this kind, however central its rol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not taught in schools. To put this point harshly, in terms of this essential new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is new lsquo;visual literacyrsquo;,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often reactionary political demands, produces illiterates.
Of course, writing is itself a form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Indeed, and paradoxically, the sign of the fully literate social person is the ability to treat writing completely as a visual medium – for instance by not moving onersquo;s lips and not vocalizing when one is reading, not even lsquo;subvocalizingrsquo; (a silent lsquo;speaking aloud in the headrsquo;, to bring out the full paradox of this activity). Readers who move their lips when reading, who subvocalize, are regarded as cultu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tainted by having to take recourse to the culturally less valued mode of spoken language when reading visual script. This lsquo;oldrsquo; visual literacy, writing, has for centuries now been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achievements and values of Western culture, and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goals of education, so much so that one major and heavily value-laden distinction made by Western cultures has been that between literate (advanced) and non-literate (oral and primitive) cultures. No wonder that the move towards a new literacy, based on images and visual design, can come to be seen as a threat, a sign of the decline of culture, and hence a particularly potent symbol and rallying point for conservative and even reactionary social groupings.
The fading out of certain kinds of texts by and for children, then, is not a straightforward disvaluatio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but a valuation which gives particular prominence to one kind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writing, and to one kind of visual literacy, the lsquo;oldrsquo; visual literacy. Other visual communication is either treated as the domain of a very small elite of specialists, or disvalued as a possible fo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文献翻译
出处:Kressamp;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 2006:p18-37
译文:
符号视角:语言及视觉交流
在教育初期,教师会不断地鼓励学生去制作图像并要求说明他们的书面作品。教师对这些图像的评论与对书中文本的评论一样,尽管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图像既不会被“纠正”,也不会受到细节化的批评(“这需要更多练习”,“表达不清晰”,“拼写有误”,“表达不准确”等等。)它们通常被视作是一种自我表达而非沟通的方式---是孩子们可以自发地做的事情,而不是作为他们必须被教导的东西。
当孩子们度过中学初期的两年时间,图像基本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从那以后,图画和写作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矛盾起来:写作变得日益重要且经常出现,而图像变得专业化。当今时代,写作和图像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的这一事实导致问题更加棘手。我们可以用二十或三十年前的情形来描述现在的情况:早期学校的课本中会穿插有大量的图片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但是小学后期的课本中图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书面语篇所取代。在图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成为具有技术功能的代表。比如说地理课本中的地图,图表或者照片描绘的是特定地貌,河口或定居点类型。因此儿童自己制作的图像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从“表达”转向技术性。换句话说,图像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功能上变得专业化。
在许多方面,学校的情况仍然是相同的,而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一方面,所有学校学科现在都更多地利用图像,特别是在中学教育阶段。 在许多科目中,尤其是具有科学和技术性的课程如(英国)科学,信息技术或地理学,图像已经成为代表课程内容的主要手段。在更人性化的科目 - 例如历史,英语和宗教研究 - 图像具有说明,装饰和传达信息等不同的功能。 这种趋势仍然存在,对工作表,教科书和只读存储器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图像并不具有教学或者指导的新角色。(尽管英国学校的信息技术课程上,桌面出版存在教学)。更重要的是,评估继续以写作为主要模式。 教师会要求学生在科学,地理和历史课上制作图画;然而和此前一样,我们可以从教师对学生 作业的(书面)评论上就可以判断图像并没有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换句话说,给学生提供的资料使用了大量具有再现意义的图片。而在对学生的材料要求中,尤其是各种形式的教学评估---写作仍然占据预期和指导模式。
然而在学校外,除文字以外,图像对儿童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无论是在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无论是在报纸,杂志,CDROM或网站,无论是作为公共关系材料,广告或各种信息材料,大多数文本现在都涉及书面文字,图像和其他图形或声音元素的复杂相互作用,通过布局将它们设计为连贯的(通常在第一级视觉而不是语言)实体。学校并没有教授生产这种多模态文本的技能,虽然它在当代社会中起着核心作用。严格点来说,这个重要的新的沟通能力,这种新式“视觉文化”-制度教育在经常反动的政治要求的压力下,产生文盲。当然,写作本身就是视觉传达的一种形式。 事实上矛盾的是,充分识字的社会人士的标志是有能力把写作完全视为一种视觉媒介 - 比如说当一个人阅读时,嘴唇不动也没有发出声音,甚至没有“默读”(安静的“在脑中大声说话”),以表现出这种活动的完全矛盾)。读书时嘴唇移动或者默读的人会被认为在文化和智力上被污染,所以不得不在阅读视觉文本时采取文化上不那么重要的口语模式。这种“古老”的视觉文化-写作,数百年来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成就和价值之一,也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样一来,西方文化所产生的一个主要和重要的价值观区别在于识字(高级)和不识字(口头和原始)文化之间。难怪根据图像和视觉设计向新的文化方向的转变被视为一种威胁,即文化衰落的迹象。因此对于保守甚至反动的社会群体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力的象征和集会点。
那么对孩子们来说,某些类型的文本的衰落并不是对视觉传达的直接的贬低,而是特别重视一种视觉交流和一种视觉文化,即对写作的估价。这不是对视觉传达的语言的评价,因为即使现在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品种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在教育制度中的多样性也不受重视(除了一些例外,例如正式的 辩论)或公开的权力论坛。
总而言之:反对视觉作为一种充分的表现手段的出现不是基于对视觉的反对,而是反对其成为写作代替物情形的出现,因此可以被看作统治精英群体中文化素养占主导地位的潜在威胁。
在这本书中,我们重新审视关于视觉的问题。 我们想要像对待语言形式那样认真对待图像中的交流形式。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了视觉传达的重要性,现在缺乏谈论和思考图像和视觉设计实际传达的方法的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摆脱罗兰·巴特在他1964年的“形象修辞学”中所采取的立场(1977:32-51)。在这篇文章中(和其他地方一样,如“语义元素”(Barthes,1967a)),他认为图像(和其他符号代码,如衣服,食物等)的含义总是有关于甚至依赖于言语文本。他自己也认为,图像也是“多义的”,对于各种可能的含义来说也是如此。为了达成一定的意义,语言必须前来救援。 视觉意义太不明确。它是一个“浮动的意义链”。 因此,巴特说,“在每个社会,各种技术的开发旨在用这种方式来修复被指定的浮动链,以抵制不确定迹象的恐怖; 语言信息是这些技术之一(1977:39)。他区分了图像文本关系,其中语言文本扩展了图像的意义,反之亦然,例如,漫画中的语音气球以及语言中的语言关系。文本有助于阐述图像,反之亦然。前一种情况,他称之为中继器,通过添加新的和不同的含义来完成信息构建。在后一种情况下,同样的含义以不同的(例如更确定和精确的)方式重述,例如在进行标题识别和/或解释照片中显示的内容时。其中,阐述是主导的。 巴特说,接力“更罕见”。他区分了两种形式,其中语言文本首先出现,使得图像形成一个例证,而图像是首先形成的,从而使文本形成一个更明确和精确的重述或“修复” (他称之为锚地的关系)。
在大约1600年之前(过渡当然是非常渐进的),巴特认为,“插图”是占统治地位的。 图像详细阐述了文本,更具体地说是文化的创始文本 - 神话,圣经,文化的“圣经” - 文本,因此可被认为是观众所熟悉的事物。这种语言文本形成社会权威的一种关系,其中以特定模式将特定文本传播给社会中的特定群体的这种关系逐渐转变为自然而不是话语成为权威的来源。在科学时代,更为自然主义的图像开始发挥“自然之书”的作用,就像作为“观察”的“世界之窗”一样,而口头文本则用来识别和解释,用文化,道德,想象力来加载图像。
这个论述点确实解释了沟通的要素。 任何一个图像文本关系。巴特的描述可能有时起主导作用,虽然我们觉得今天有离开“锚地”的一个举动。例如,在比较“经典”的纪录片中,观众首先面对的是“自然的图像”,然后辨识和解释图像的叙述者的权威声音与现代的“时事”项目。 观众首先面对的是主持人的言语话语,或者是同时或者后续的口头表述,与“自然的图像”一起说明、例示和认证话语。 但巴特的评述错过了重要的一点:文本的视觉组件是一种独立的且有组织和结构化的信息,它与语言文本相关联,但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文本 - 同样的方式也是相反的。
我们在这本书中的叙述和早期的符号学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在于我们在语言理论和语言描述中使用了工作。这个论点很难提出,但值得我们论述。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语言学的成就,这本书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我们并不赞同有些批评者认为我们的方法属于语言学方法的一种。所以我们从语言学中使用了什么,我们如何使用它? 同样,我们没有从语言学中使用什么?从后一个问题开始,我们还没有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导入视觉领域,正如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其他人所做的一样。例如,我们不会在视觉领域中分离语法,语义和语用;我们不在图像中寻找(类似的)句子,子句,名词,动词等。 我们认为,语言和视觉传达都可以用来实现构成我们文化的“同一”基本的意义系统,但是每个都是通过自己的具体形式来实现,形式不一而且独立。
举一个例子,自从物理科学在十六世纪开始发展以来,“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区别在西方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区分可以通过语言和视觉手段实现(即具体的,物质的表达,因此可以被感知和传播)。因此,“主观”和“客观”这两个术语可以适用于两者:它们属于文化及其社会的意义潜力。但是,利用语言实现区分的方式与图像中实现的方式截然不同。例如,在语言中,一个想法可以通过使用像第一个人那样相信的“心理过程动词”来主观地实现(例如,我们认为有一种图像的语法); 或客观地通过不存在的形式(例如,存在图像的语法)。客观来说,该观点则将在第四章中进一步讨论。心理过程语句和名义化是语言独有的。 而透视图则是图像的独特之处。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所表达的意义都来自于相同的广泛领域; 在同一时期,因为同样的文化变迁会形成与之相同的文化形式。语言和视觉传达都表达了一个社会中属于文化和结构的意义; 符号学过程虽然不是符号学的手段,但是大致相似;这导致两者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然而,与此同时,每种媒介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局限性。不是所有可以用语言实现的东西也可以通过图像来实现,反之亦然。除了广泛文化的一致性外,两者(和其他符号模式当然)之间存在显着差异。比如在英语这门语言中,通常需要使用一个动词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话语(相信,是);并且语言必须使用名称来引出所要表示的内容(图像语法,相信,我们)。但是,语言并没有或需要利用视角来提出观点,也没有或需要空间元素分配来实现句法关系的含义:图像二者都需要。这两种模式的意义潜力既不完全混淆也不完全相反。 我们不同于那些把语言意义看成是从语境中衍生出来的形式和意义上的内容或语言含义的人。
回到我们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 - 我们从语言学中使用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它?也许最重要的语言是我们的整体做法,一种“态度”,它认为图像作为一种呈现的资源会和语言一样具有规律性,这可以作为相对正式探究的主题。我们称之为“语法”,并关注文化生产的规律性。更具体地说,我们借鉴了“符号方向”,不管模式如何,我们把它们视为对所有人类意义的概括。例如,我们认为,“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符号学问题,可以在语言和视觉上实现。尽管如此,但还是存在不同之处。或者,作为另一个例子,我们把迈克尔·哈利迪的社会符号学方法作为模型,将其作为一种思考一般社会和符号过程的来源,而不是将类别应用于图像描述中。他的三个功能的模型是我们描述图像的起点,不是因为该模型对于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而是因为适用于作为思考所有代表模式的来源。
也许最重要的观点是:我们的交流方式源于社会基础。在我们看来,即使我们承认个人差异的影响和重要性,发言人,作家,版画家,摄影师,设计师,画家和雕塑家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社会意义。鉴于社会中的群体不是同质的,社会是由具有不同甚至是矛盾利益的群体组成,个人产生的不同信息将反映出社会生活特征的差异,不协调和冲突。根据我们的经验,通常情况下,文本构建的不同模式会显示出这些社会差异,因此在使用图像和书写文字的多模态语篇中,文本可能会具有一种意义,而图像具有另一种意义。例如,在广告中,口头话语可能具有性别歧视的含义,而视觉文本则是公开地表达性别歧视的定型观念。鉴于图像意义仍然普遍存在,我们可以假设图像中所携带的意义仅存在于“旁观者眼中”,而不能口头判定文本实现的意义。
我们在这本书中用到的例子取自很多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想法能够帮助任何有兴趣的人通过图像来观看图像,不仅在美学和表现方面,还有结构化的社会,政治和交际层面。我们将从已经完全基于新的视觉文化的文本中提取示例,并在任何公共领域,杂志文章,广告,教科书,网站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不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些文本推广成一种应该替代其他文本的模式,而是因为他们在儿童和成年人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能让少数专家考虑和谈论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生产他们)。我们对儿童生活中的视觉领域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尽早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尽管有很多鼓励)去发展使用视觉语法中各要素的能力。- 我们认为应该更好地理解和进一步发展孩子的这种能力,而不是过早地遏制其发展; 以及成人也可以具有的能力。
在传统的写作史上,语言,书面媒介相对于其他视觉媒体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坚定的编码和支持。这些就像这样。言语形式是所有人类共同的自然现象。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26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中国古诗词的意象表达与翻译——以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词译著为例开题报告
- 论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豪杰译现象——以《黑奴吁天录》及《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文献综述
-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Tourism Translation开题报告
- “言语”和“静默”外文翻译资料
-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电影翻译的力量外文翻译资料
- 从个人成长视角分析《追风筝的人》中的主角阿米尔的人物性格外文翻译资料
- 个人旅游博客作为研究跨文化交往的文本:来自津巴布韦的美国sojourner博客的试点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接受理论视角下动画电影字幕翻译的比较研究 –以《疯狂动物城》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On DifferenceTranslation Of E-C Plant Metaphors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