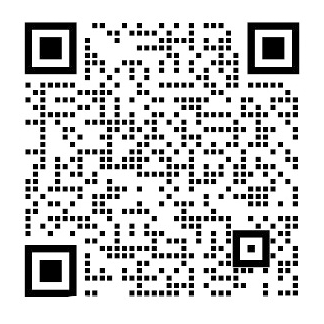选自: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Vol.1, No.1, 2010, pp.19-24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lf in Desire under the Elms
XIE Qun1
Abstract: As a masterpiece of Eugene Orsquo;Neill, Desire under the Elms challenges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interpretation. Employing Charles Taylorrsquo;s theories of ethic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moral stat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play. Though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culture of utilitarianism, Eben and Abbie canrsquo;t find happiness in pure material possession and physical pleasure. In their competition for wealth, they come to recognize a more enduring power that may bring purgation to greediness and spiritual fulfilment, that is, the good originated from Christianity. Inspired by the power of this good – the other-regarding love, both Eben and Abbie give up selfishness and material desire and gradually achieve a self transformation. The changes that occur on the two characters reveal one of Orsquo;Neillrsquo;s major concerns in his dramatic creation: the moral confusion of modern man in America.
Key words: Eugene Orsquo;Neill; ethics; the good; utilitarianism
As a masterpiece of Eugene Orsquo;Neill, Desire under the Elms provides a picture of the modern self inhabiting in a society dominated by instrumental capitalism. The Cabot farm is rendered as a world cold and sterile where everyone lives for onersquo;s self and in defense of the other selves. Family intimacy and mutual concern for each other are absent among the Cabotrsquo;s. Ephraim Cabot makes his wives and his sons slaves to the farm. As a result he receives no affection from his family. So he feels lonely and cold. In the evening coldness and loneliness drives him to sleep with the cows instead of his wife. Simeon and Peter feel their lives have been spent on building stone walls for their father to imprison them. Eben feels double hatred to his father for “murdering” his mother with hard work and for stealing the farm from his mother. In his relation with his two brothers, Eben only cares for how to obtain their shares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farm.
What Orsquo;Neill deals with in Elms is a problem encountered by the modern self after the loss of religion.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used to serve as the spiritual support for people. It allows room for different high values and spiritual pursuit. In an age of disenchantment, man is gradually cut off from this divine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ropels the society to lean on instrumentalism.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especially in America, the utilitarianism takes the form of egoistic material possession. This is the culture that Orsquo;Neill abhors and criticizes in many occasions. In an age dominated by utilitarianism can man retain moral integrity? Is the good of Christianity really dead with the death of the god? Can man live with utilitarianism as the sole purpose of life? The answers have to be retrieved from the text.
Charles Taylor has discusse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xtreme instrumentalism in his Sources of the Self. He points out that “a utilitarian value outlook is entrenched in the institutions of a commercial,
1 Jiangxi Ganjiang Vocational College, China.
* Received 15 February 2010; accepted 10 April 2010
capitalist, and finally a bureaucratic mode of existence, tends to empty life of its richness, depth, or meaning,” and “nothing is left which give life a deep and powerful sense of purpose. (SS 500) In this case there will be no room for heroism, or aristocratic virtues, or high purpose in life, or things worthy dying for. (SS 500) A purely instrumental stance that only concerns the utilitarian sides and material aspect of things will consequently lead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piritual side and ultraistic aspect of human vision, while for human beings these represent indispensable part of intrinsic value. (SS 500)
Human life empty of its richness, depth and meaning is reflected in the Cabots family. Being occupied with egoistic possessiveness, the Cabots live on nourishment of desires. Ephraim Cabot is indulgent in his insatiable desire for land and wealth. The two elder brothers Simeon and Peter dream of gold in California. Eben is obsessed with his desire to regain his motherrsquo;s farm and to avenge his father who has worked his mother to death. Abbie marries the old Cabot out of her desire for a home. In the meantime, all of them share a desire for warmth and sexuality. This desire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Cabot menrsquo;s relationship with Minnie, the Scarlet woman in the village, and in the inc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Eben and his stepmother Abbie. The elder son Simeon claims that “we air his [Cabotrsquo;s] heirs in everythin!” Being kept from the high values and high purpose of life, and being possessed by insatiate desires, the Cabots lead a life that degenerates into that of the animals. Orsquo;Neill emphasizes the animal-state of life through the language of the characters.
The desires that energize the Cabot are self-oriented, arising out of self-satisfaction either physically, materially or psychologically. Such desires have substantiated the self in the play and function to make the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inner-dri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lay, the three brothers all perceive the presence of a driving desire in their lives. First, they identify this force as the cause that motivates their fatherrsquo;s cruel enslavement of the whole family. Simeon says: “Itrsquo;s somethinrsquo; – drivinrsquo; him – trsquo; drive us!” (I.ii, 323) In his statement Cabot is perceived to be in a state of behaving involuntarily, which constructs a threat to the brothers because such a state may end up with lose of self-control. They fear an impending destruction to all of them. For this reason Peter accuses his father: “Hersquo;s slaved himself trsquo; death. Hersquo;s slaved Sim lsquo;nrsquo; mersquo;nrsquo;yew trsquo; deat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自我转化
谢群
摘要:作为尤金bull;奥尼尔的杰作,《榆树下的欲望》挑战了时间和解释的局限性。采用查尔斯bull;泰勒的伦理学理论,作者探讨了剧中主要角色的道德状态。埃本和爱碧虽然深受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但在纯粹的物质享受和生理愉悦中找不到快乐。在他们争夺财富的过程中,他们开始认识到一种更为持久的力量,它可能去除贪婪,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也就是源于基督教的善。受到这种善的力量以及其他关乎爱的激励,埃本和爱碧都放弃了自私和物质欲望,并逐渐实现自我转变。这两个角色发生的变化揭示了奥尼尔戏剧创作中的一个主要关注点:现代美国人的道德迷茫。
关键词:尤金bull;奥尼尔;伦理;善;功利主义
作为尤金·奥尼尔的杰作,《榆树下的欲望》提供了一幅现代自我在由工具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中居住的图景。卡博特农场被渲染为一个寒冷和无菌的地方,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并且防范别人。卡博特的家人之间缺乏亲密关系和彼此关怀。卡博特让他的妻子和儿子成为农场的奴隶,结果他没有受到家人的喜爱,所以他感到孤独和冷漠。夜晚的寒冷与孤独驱使他与奶牛睡在一起,而不是他的妻子。西蒙和彼得觉得他们的生命花费在为父亲建造石墙从而监禁了他们自己。埃本对他的父亲感到双重仇恨,因为他父亲让母亲辛苦工作从而“谋杀”了他的母亲,并从母亲那里偷走了农场。在与他两个兄弟的关系中,埃本只关心如何获得农场遗产的份额。
奥尼尔在《榆树下的欲望》中所处理的是在失去宗教信仰后现代自我遇到的问题。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曾经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它为不同的高价值和精神追求提供了空间。在一个觉醒的时代,人们逐渐被剥夺了这种神圣的力量。 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依靠工具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美国,功利主义以利己的物质占有为形式。这是奥尼尔多次憎恶和批评的文化。在功利主义主宰的时代,人能否保持道德的完整?基督教的好处是否真的因神的死亡而死亡?人可以以功利主义为生活的唯一目的吗?答案必须从文本中找到。
查尔斯·泰勒在他的“自我之源”中讨论了极端工具主义的后果。他指出,“功利主义价值观根深蒂固于商业、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是官僚式的生存方式,倾向于将生命的丰富性、深度和意义排除在外,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给生活带来深刻而强烈的目的感。(SS 500)在这种情况下,英雄主义、贵族美德、高尚生活目标和值得期待的事物将没有余地。(SS 500)纯粹的工具性立场只涉及事物的功利主义和物质方面,因此会抑制人类视觉的精神方面和极端方面,而对于人类来说,这些是内在价值不可缺少的部分。(SS 500)
卡博特家族体现了人生丰富、深度和意义的空虚。老卡博特充满自私的占有欲,活在欲望的滋养上。他放纵了对土地和财富的无尽渴望。两个哥哥西蒙和彼得梦见加州的黄金。埃本渴望重新获得母亲的农场,并向曾让母亲工作的父亲报仇。爱碧嫁给老卡博特出于她对家的渴望。与此同时,他们都有着对温暖和性欲的渴望。这种欲望还在卡博特与村里的女人米妮的关系,以及埃本与继母爱碧之间的乱伦关系中表现出来。卡博特家族被生活的高价值和高目标所束缚,被贪婪的欲望所笼罩,过着退化为动物的生活。奥尼尔通过人物的语言强调生命的动物状态。
激发卡博特的欲望是自我导向的,由身体、物质和心理上的自我满足产生。 这种渴望证实了自我在戏剧和功能上的作用,使角色看起来是内在驱动的。在剧中一开始,这三兄弟都认为他们生活中存在一种驱使的欲望。首先,他们认为这种欲望是促使他们父亲残酷地奴役整个家庭的原因。西蒙说:“这是事端——驱动他——驱动着我们!”(I.ii,323)在他的声明中,卡博特被认为处于非自愿行为状态,这对兄弟构成了威胁,因为这样的状态最终可能会失去自我控制。他们担心自己受到伤害。基于这个原因,彼得指责他的父亲:他自己不会死。他是死亡的奴隶。其次,这种欲望被三兄弟自己视为驱动力。他们不仅表现得好像被驱使一样,而且意识到他们被动力所操纵。推动力表现在他们对土地和黄金的无尽渴望。埃本问他的兄弟们:“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什么事情了?”(I.ii,323)西蒙和彼得回答“黄金”。这个词的选择表明他们在面对驱使欲望时承认自己的被动状态。 主角埃本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受驱动的动物。 当埃本听到他父亲再次结婚时,他疯狂地去了找米妮。
埃本的疯狂行为因他对农场的渴望而激起。父亲的婚姻意味着农场可能会落到新妈妈手里。无法收回农场,他把他父亲的女人当成替罪羊。当他描述他指责米妮的行为时,他意识到自己像“小牛”一样的状态——一只动物在冲动而不是理智的情况下行事。自我驱动的状态预示着卡博特家族的悲剧结局。正如弗洛伊德所阐释的那样,“卡博特家族被一种强大的,迷恋性的贪婪所消耗,致使他们相互剥削对方和土地。对奥尼尔来说,无视贪婪和欲望,使这些清教徒士气低落,最终导致他们堕落。”(《新评估》275)
当物质占有和利己主义的满足成为生活的唯一目标时,人类就会成为不合理行为的内驱力动物。显然,奥尼尔将黄金军舰视为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形式,作为阻碍人类行动的非人化力量。 这就是他撰写对美国文化严厉批评的原因:
美国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而是最大的失败。这最大的失败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一切,超过了其他国家hellip;hellip; 它的主要思想是通过拥有它之外的东西来试图拥有你自己的灵魂的永恒游戏。(《奥尼尔,儿子和艺术家》577)
“灵魂”被认为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这是人内在的另一个术语,也是人类的精神品质。奥尼尔在他的国家所观察到的是,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极端形式剥夺了其他人的价值,特别是在精神层面。奥尼尔认为那些完全占据物质所有者的人是没有灵魂的人,因为他们的灵魂被无尽的欲望所占有。
戏剧中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是普遍而压抑的。然而,在人性中,有些东西是无法压制或连根拔起的。现代人不是一个道德良善的后代。泰勒强烈主张现代认同由源自三种道德来源的不同产物构成。因此,“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是有很多需要承认、执行和追求的物品。这些东西不仅是数字意义上的复数,而且在本体论意义上也是复数形式;他们彼此是不同的类型,因此,它们并不会总是和谐地组合,排序或减少到某种更终极的或基础的状态。(Ruth 12)这种不同的商品也可以在剧中被识别出来,特别是在两个主角之间。
像地平线上的罗伯特一样,埃本对他的归属一无所知。 在他的兄弟眼中,他是他父亲的“吐口水”形象。 但他知道他是不同的。物质拥有不能给他带来幸福。埃本认为自己完全是他母亲的继承人——“我是妈妈的——每一滴血都是!”(I.ii,322)。批评家注意到埃本拥有的特殊品质,这使他与其他卡博特不同。博加德注意到,埃本正在寻求他的身份,因为他需要归属。
他无精打采地在陌生的地方,寻求与自然相同的身份。在厨房里,女人的世界里,在那里他无法生根。他的愿望使他与更加硬化的灵魂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他们意识不到,所以需求较少。(《时间的轮廓》209)。
埃本对他身份的失望源于他对父母的双重继承。埃本虽然受到他父亲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影响,但他也承受着母亲的影响。埃本的母亲被描绘成一位热爱自然的女性,“对每个人都很友善”。在她的沉默和耐力中,她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整个家庭,并在疲惫中消失。她的死亡象征着没有爱与仁慈。但是她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于农场中,正如剧中所展示的那样,无论是以保护榆树形象的形式,还是作为房间中无形的幽灵。埃本对母亲的认同不知不觉地揭示了他对无私的爱的渴望和肯定。但是这个关于自我的真理对埃本本人来说是隐藏的。 在爱碧的帮助下,在这种茫然消失之前,他不会看到真相。
埃本和爱碧开始是两个试图利用对方的自我主义者。正如多丽丝·福尔克所分析的那样,埃本“不是靠爱来吸引爱碧,而是靠情欲,贪婪和复仇的欲望。”(96)同样,爱碧对埃本的兴趣来源于欲望和偷窃农场的阴谋以及孩子。尽管如此,随着两人坠入爱河,利己主义动机转化为新感觉。面对爱碧,埃本发现自己发生了不知情的变化。这种变化有赖于他们通过语言传播的交流。泰勒认为我们的道德意识来源于我们与其他对话者的对话。他澄清了语言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如下:
一个人不能独立自主。我只是与某些对话者有关的自我:一方面是与那些对我实现自我定义至关重要的谈话伙伴有关;在另一个与那些对我持续掌握自我理解语言至关重要的人有关(SS 36)。
通过语言,另一位对话者,包括过去和现在,可能已经影响并将继续塑造我的身份。如果我们把埃本的母亲作为一个过去曾经对埃本传递了超凡爱情的母亲,那么爱碧成为现在的对话者继续影响着埃本。当爱碧讲述她不幸的经历时,埃本感动了。他必须对抗他对她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和同情。这个动作暴露了他对爱碧的复杂情绪。虽然她仍然是他的对手,他的反感正在超越同情和吸引力。语言具有唤起隐藏在我们内心感受的魔力,而这种感觉反过来又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道德立场。朗已经注意到了爱碧和埃本的成长。他看到“改变在欲望的激情中慢慢产生,这种激情完全变为爱的激情”(113)。 埃本的同情暴露了他抑制爱情的潜力。当爱碧要求他与她成为朋友时,尽管有自我意识,他却“被催眠”。爱碧与埃本联合的客厅场景展示了语言如何化解拥有性反感的硬壳,并释放渴望爱和被爱的自我。值得注意的是,在爱碧试图说服埃本真诚的爱情方面,母亲的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初,埃本蔑视爱碧,试图抵制她的诱惑。当爱碧扮演母亲的角色来说服埃本,她会代替他的母亲来爱埃本,一切就会发生变化。
爱碧: 跟我说说你母亲,埃本。
埃本:没什么,她很善良,也很好。
爱碧:[把一只手臂放在他的肩膀上。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也会善良和友好的!
埃本: 有时候她会唱歌给我听。
爱碧:我也会唱歌给你听的!(II.iv,355)
在这场对话中,爱碧一直说服埃本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爱碧已经认识到埃本的爱情饥饿,他需要爱和被爱。她正在努力让自己成为埃本的爱人。在剧中,爱和被爱被暗示为人性。 这就解释了爱碧提醒埃本——“自然会打败你,埃本”。爱碧所做的是试图唤起埃本屈服于自己的爱情。
与此同时,当爱碧认定自己是埃本的母亲时,她也表明,爱和被爱是她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母亲的爱代表了最无私和纯粹的人类情感。因此,通过母亲的形象,奥尼尔用一种道德力量与功利主义相对立,即基于他人的基督教价值——在爱和自我牺牲方面注入了戏剧,与表现冰冷的父亲卡博特的功利主义自我力量形成对比,其他关于爱的道德力量与母亲的温暖和自然的活力(人性)相关联。
他们不协调的关系发生在客厅的情节,这成为他们不幸误解的来源。当爱碧与埃本的母亲认同自己的爱和奉献的承诺时,她的爱和牺牲的本性被完全唤醒,并且她真正变成了一个脱离自我主义的女人。在“自我解读动物”中,泰勒指出:
说人是一个自我解释的动物,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些强迫性的倾向来形成对自己的反思性看法,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部分由自我解释构成的......(Human Agency 72)
他还指出:“我们的自我(错误)理解塑造了我们的感受。”(Human Agency 65)自我的阐释带来了自我解释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自我。爱碧的自我诠释引导她拥抱一个新的自我,一个能够爱与牺牲的女人。但在埃本的一部分,他仍然被关在他自私的笼子里。如果没有认识到爱碧的真诚和他自己需要爱和成为爱,他就会把他与爱碧的关系理解为对卡博特的报复——从他母亲的意志中跳出来。 对他而言,与爱碧做爱只不过是一种报复行为。埃本没有认识到爱碧的爱情以及他对爱碧的热爱,成为他们悲剧的原因。
由于埃本并没有抛弃对拥有的渴望,在与爱碧的关系中,他的感觉是模棱两可的。他对她的爱逐渐增长。但他无法完全忠于他的爱。爱碧对他的财产仍然构成潜在威胁。这种矛盾的情绪和他的道德立场的不确定性使他成为以法莲戏弄的简单牺牲品。因此,当老卡博特揭示出爱碧打算用她的新生儿占有这个农场时,埃本又重新看到了他的老自我,他从一个功利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角度看待了一切。 考虑到他被爱碧欺骗并被用作偷窃农场的工具,埃本发出谴责爱碧和她的孩子的声音,说他希望孩子从未出生。埃本的不信任最终导致了爱碧的杀婴作为她纯洁的爱的证明。
改变埃本的力量来自爱碧对他毫无保留的爱。在爱和被爱中,她完全放弃了自私和占有欲。爱碧已经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她在最后一幕中的表现表明她赞同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最后一幕中,尽管她因杀婴而面临死亡或监禁,但她依然专注于埃本。 即使埃本去找警长,她也会跟他说:“我爱你,埃本! 我爱你们! 我不在乎你们做了什么!“(II.iv.371)爱碧从功利主义者转到极端主义者使她能够理解埃本对警察的背叛。由于卡博特贬低了埃本背叛埃本的行为,她为他辩护。爱碧不仅能够理解埃本,也愿意原谅埃本。放弃所有的贪婪和占有欲,爱碧在爱和宽恕中找到满足和快乐。她的无私奉献和爱心最终将埃本带入了顿悟的自我认知。
最后一幕终于埃本跑回去找爱碧,充分认识到他对她的真爱。在这个时刻,他在道德立场上被爱所改变。如果过去他被诸如财产和欲望等各种自私心理所蒙蔽双眼,现在他开始看到他追求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他发现了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到爱碧已经杀害了宝宝以保持他的爱情,他要求爱碧原谅他,并愿意与她分担罪恶。逮捕前的对话揭示了埃本发生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埃本经常使用“我的”代词来捍卫他的财产相比, “你”在埃本的言论中占据了显着的位置。在他的关注中,拥有“你”意味着埃本已经脱离了他的利己主义的自我,获得了利他主义的观点。现在他的自我意识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另一个自我爱碧联系在一起的。查尔斯·泰勒强调了认同感的重要性。他说:“要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在哪里。我的身份是由承诺和标识定义的,这些承诺和标识引起我可以尝试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应该做什么,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框架或范围”(SS 27)。 通过他对爱碧的道义承诺,终于认识到对他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他的语言表明他已经在其他关于爱情方面找到了幸福与和平。他声称,与爱碧分享罪恶和死亡,他不会感到孤独。朗已经认识到埃本转型中的宗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136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中国古诗词的意象表达与翻译——以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词译著为例开题报告
- 论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豪杰译现象——以《黑奴吁天录》及《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文献综述
-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Tourism Translation开题报告
- “言语”和“静默”外文翻译资料
-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电影翻译的力量外文翻译资料
- 从个人成长视角分析《追风筝的人》中的主角阿米尔的人物性格外文翻译资料
- 个人旅游博客作为研究跨文化交往的文本:来自津巴布韦的美国sojourner博客的试点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接受理论视角下动画电影字幕翻译的比较研究 –以《疯狂动物城》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On DifferenceTranslation Of E-C Plant Metaphors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