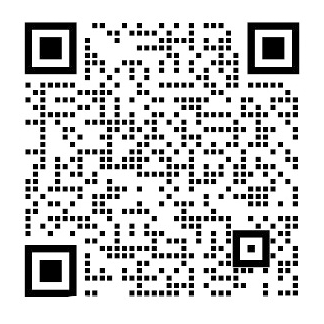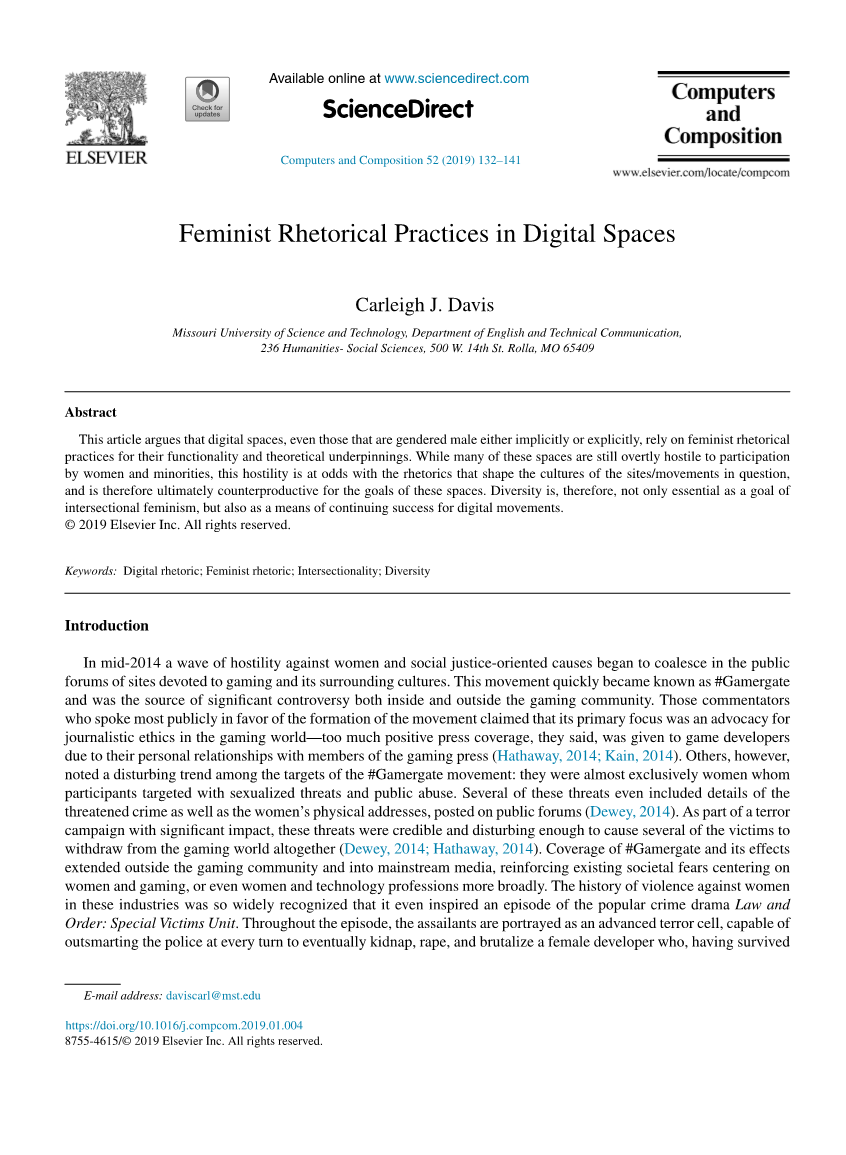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0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数字空间中的女性主义修辞实践
Carleigh J. Davis
密苏里科技大学英语与技术传播系,236人文社会科学,500 W. 14 St. Rolla, MO 65409
计算机与合成52 (2019)132-141
摘要:本文认为,数字空间的功能和理论基础依赖于女性主义的修辞实践,即使是那些含蓄或明确性别化的男性空间。虽然这些空间中有许多仍然公然敌视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参与,但这种敌意与塑造这些场所/运动文化的修辞不符,因此最终不利于这些空间的目标。因此,多样性不仅是跨部门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数字运动持续成功的一种手段。
介绍
2014年年中,一波针对女性的敌意和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事业开始在致力于游戏及其周边文化的公共论坛上融合。这一运动很快被称为#Gamergate(游戏门),并在游戏社区内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些最公开支持该运动成立的评论家声称,该运动的主要焦点是在游戏世界中倡导新闻伦理,他们说,由于游戏开发者与游戏媒体成员的私人关系,游戏开发商获得了太多正面的媒体报道(Hathaway, 2014;Kain, 2014)。然而,也有一些人注意到,在Gamergate运动的目标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几乎都是女性,她们是参与者受到性威胁和公开虐待的目标。其中一些威胁甚至包括被威胁犯罪的细节,以及公布在公共论坛上的女性身体地址(Dewey, 2014)。作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恐怖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威胁是可信和令人不安的,足以导致数名受害者完全退出游戏世界(Dewey, 2014;haway, 2014)。Gamergate及其影响的报道已扩展到游戏社区之外,并进入主流媒体,强化了围绕女性和游戏、甚至更广泛的女性和技术行业的现有社会担忧。在这些行业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历史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承认,以致于它甚至激发了流行犯罪剧《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股》的一集。整个事件,袭击者被描绘成一个先进的恐怖细胞,能够超越警察每次最终绑架,强奸,并残酷地对待女性开发人员,经过她的可怕的折磨,决定离开游戏世界规劝,“妇女在游戏,我希望什么?”,业内人士和游戏爱好者肯定的法律和秩序的描述是荒谬的(Merlan, 2015),事实上,它利用一些现有的观念,外人(和未来潜在的参与者)关于世界博彩业作为黑客文化和数字空间不仅更多地敌视女性,但足以在敌意的行为而不受惩罚。
尽管不同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人总是参与技术发展,但他们的贡献往往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因此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围绕数字工具及其发展的历史叙事往往强调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的联系(Millar, 1998;Wajcman, 2010)。这些人对创造性项目开发的压倒性的获取和控制,既掩盖了参与这些项目的人的贡献,又缺乏他们的社会特权,而且有效地将现有的白人、异性恋、男性主导的文化规范,转变为正在开发的数字工具(最近广为宣传的一个例子是,参见2016年的电影《隐藏的人物》(Hidden Figures))。其结果是一种数字文化,被认为是男性的性别。由于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系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这些准入障碍在一些数字文化中已经演变成一种态度,在这些文化中,参与者渴望回到技术
发展的“黄金时代”——一个想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只是关于技术,与具体问题没有交叉(关于驳斥这一观点的学术研究,见Turkle, 1995;amura, 2008;Hayles, 1999;Reilly,2004)。
这种意识形态与同样虚构的公正理想和数字系统固有的公正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综上所述,对数字工具的有用性或可用性的无实体感知,以及这些工具是价值中立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假设:在数字社区中,任何涉及到与技术相关的实体问题的尝试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会适得其反。换句话说,如果技术是基于逻辑的,那么它已经“适合所有人”(即:适合所有符合规范社会模式的人),因此没有必要在性别、种族、性或其他体现问题上不合逻辑地偏向技术系统。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数字文化的扩散,这些文化对那些在假定的白人顺式男性规范之外进行身份识别的参与者怀有敌意,因为通过这种身份识别,这些参与者被标记为有形体的个体,因此(根据这些系统的逻辑)与定义技术的无形体纯粹性截然相反。这些定义她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在4chan/anonymous这样匿名的空间和#Gamergate这样的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并通过骚扰运动和媒体对她们尖刻言论的报道,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在以数字为基础的行业,女性既不受欢迎,也不安全。
这些态度所代表的威胁是真实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威胁是影响女性进入数字空间的合法障碍。不同的种族和社会经济人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障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每个人身上。然而,数字文化也以多种方式在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基础上蓬勃发展,重要的是要平衡这些叙述,以避免阻碍代表性不足的人群参与数字或基于技术的领域。虽然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减轻限制使用数字工作空间的因素,但对无法找到可以认可和赞赏贡献的空间的担忧不应加剧这些本已令人担忧的情况。数字修辞学的学者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这使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些空间中发生的修辞学实践,并向不同的参与者发出欢迎信号,同时也强调了数字发展中这种多样化的必要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数字空间(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各样的网站、节目、节目团体和多派运动),甚至一些隐含或明确性别的男性,可能会在其发展和功能中采用女权主义的修辞手法。这些实践构成了这些空间运作的核心,往往也构成了这些空间明确表述的价值,但它们的女权主义根源却没有得到承认。虽然在数字空间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女权主义修辞实践来履行这一角色,但我选择将本文的分析重点放在对话协作、通过广泛扩散的社会干预,以及多样性上,尤其是因为它们的女权主义价值观在运作中被微妙地掩盖了。因为这些实践是如此广泛的数字交互,很容易把它们作为特征只有数码性而不是数码性和女权主义,它允许参与者忽视意识形态断开出现在空间,拥抱这些女权主义实践但未能遵循他们创建其最终结论的逻辑,这是增加多样性。承认这些实践的女权主义根源,有助于促进这些空间赖以运作的多样性,同时也能消除妇女和少数群体参与这种知识创造的耻辱。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首先承认数字修辞学学者已经开始呼吁让数字空间对不同参与者更具包容性。在对现有学术的简要回顾中,我指出,当前的文献在讨论女性在数字空间中互动时遇到的陷阱和女性在促进传统女性工作的空间中创造和运营的成功故事之间摇摆不定。在此基础上,我将讨论植根于女权主义修辞传统的三种不同的实践,它们塑造了数字空间中的哲学和互动的可提供性,而不管它们的性别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这些实践包括对话协作、通过广泛扩散的社会干预和多领域性。对每一种做法的讨论都伴随着一项案例研究,该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这些做法的实施情况,但这些案例只是作为说明性的例子;简单的比较将显示出在几乎所有数字环境中类似的实践。我选择这些案例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有关实践的清晰说明,同时也代表了各种明确陈述的意识形态、受众和积极参与者。我将首先分析开源软件运动对对话协作的依赖,以论证不同的视角对于程序设计的进步是必要的,并且从理论上讲,开源软件运动的反专有价值促进了那些无法负担这种交互的人群的访问。接下来,我探讨了通过广泛扩散的社会干预,#TransHackFeminist的Gynepunk团体试图利用互联网重新夺回对女性医疗保健的控制权。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它展示了协作分发和交互能够与互联网的启示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的方式。最后,我将研究Code.org如何使用多种特性作为教学工具,通过强调体现和个性,向不同的小学生群体推广编码。这种强调鼓励学生把他们独特的具体化特征和体验的组合看作编码过程的资产,从而对普遍存在的数字化工作固有的非具体化和/或不欢迎多样性的观点提出质疑。
这些空间远非完美,但它们和其他许多空间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女性主义包容性的实践如何存在于数字工具和空间的语言和设计中,并可能成为打破主导这些空间的常见男性主义观念的突破点。由于拒绝承认这些实践,我们无法向潜在的新来者和那些已经从事数字工作的人发出信号,即数字性和多样性是相互建设性的。我们作为数字修辞学家应该承认并探索女权主义修辞实践的方式塑造数字空间的工作方式与偏见,使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数字字段和关注的方式应该允许这些参与者提供的不同的观点来帮助这些领域成长和繁荣。
数字修辞学与写作中的包容性动作:对现有文献的回顾
数字空间对女性怀有敌意或不受欢迎的持久观念,并没有被数字修辞和写作领域的学者所忽视。这些学者历来注意到男性在技术相关领域的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对科学和技术存在先入之见,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以男性为导向的,并受到阻碍女性在其团队中出类拔萃的做法的驱动(Aschauer, 1999;Beck, Blair amp; Grohowski, 2015;st amp; Haas, 2017)。Aschauer特别关注于确定学者们克服可能阻碍女性在基于技术的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不适的方法,方法是将新的研究重点放在使用技术工作和写作的女性的现有实践上(Aschauer, 1999)。从这项研究中,其他人展示了被排除在这些空间之外可以通过影响社会权力动态来限制女性在生活的其他领域的自主权(Blair amp; Takayoshi, 1999;st amp; Haas, 2017; Hocks1999;amura, 2008)。在数字修辞学和写作领域,大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这一目标上,试图通过识别和参与教学实践来培养更具包容性的课堂空间,并希望通过扩展来鼓励更多女性积极参与数字沟通(Alexander amp; Banks, 2004;Haas, Tulley amp; Blair, 2002;LeCourt amp; Barnes, 1999;Takayoshi Huot amp; Huot, 1999)。
然而,教室并不是唯一需要关注和机会的地方。再次利用Ashauer关于女性已经在数字空间中成功互动的呼吁(尽管与她对职场的关注略有偏离),几位学者进行了研究,证明了在线论坛中创建的女性友好(或女性主导)空间是强大的空间,女性可以在其中培养关系,并以自己的方式构建知识(Blair amp; Takayoshi, 1999;Cherny amp; Weise, 1996;e amp; Breault, 2002;杰拉德,2002;ks, 1999;Hawisher amp; Sullivan, 1998;livan, 1999)。这种成功的一个特殊例子可以在DigiRhet (DigiRhet.org.)这样的协作项目中找到。最近,Kristine Blair、Radhika Gajjala和Christine Tulley(2009)编辑了《网络女权主义实践:社区、教育和社会行动》一书,探讨了女性在数字媒体中与媒体互动和扮演媒介角色的方式。
Gruwell(2015)指出一个特定障碍此类活动时,她的成功演示了如何实践和在维基百科网站互动功能的模式培养的排斥女性的声音,故意与否,从而打开门类似的观察各种数字论坛,即使是那些专门设计的包容性。其他障碍包括Main(2001)在她的书《性高潮技术》中提到的:“歇斯底里”、振动器和女性的性满足;也就是说,当女性获得并控制这些技术时,人们往往会认为这些技术的价值更低或更先进。维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 Eubanks, 2012)在她的著作《数字死胡同:信息时代为社会正义而战》(Digital Dead End: Fighting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中分析并寻找了打破这些技术的方法,这些技术与性别、种族和阶级有关。
对话的合作
长期以来,合作一直被视为女性主义写作实践的基石(Jarratt amp; Worsham, 1998;Lunsford amp; Ede, 1990;Ervin amp; Fox, 1994)。协作显然最明显的形式的开发和操作数字空间朗斯福德和爱德称之为对话的协作、松散结构形式的协作,参与者分享项目建设投入的想法在一起而不是依靠一个层次结构允许一个人最终的决策过程。Lunsford和 Ede在他们的“新关键中的修辞:妇女与合作”一章中写道,“在对话合作中[hellip;hellip;],集体努力被视为对知识的生产(而不仅仅是恢复)至关重要,而且是群体内个人满足的一种手段。这种合作模式[hellip;hellip;]至少潜在地极具颠覆性”(236)。对话合作的颠覆性在于它反对传统的男权主义的所有权和权威观念;当对一个项目或一个想法的贡献在许多参与者之间传播,这些参与者的角色不断变化时,将作者或所有者分配给结果就变得困难得多(Lunsford amp; Ede;Flynn等)。同样,Lunsford和Ede注意到对话协作模型通常更有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为项目带来了多种视角。他们解释说,“那些参与层级协作的人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项目中存在多个视角、声音和权威),这些人(重视对话协作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利用和强调的优势”(236)。显然,这些视角之间的差异越大,协作实践在该模型中就越有价值和生产性。
这种合理性——无论是作者身份还是效率——在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数字空间中都很明显,当我们检查绝大多数代码编写实践(团队或个人将他人编写的代码行拼接在一起,修改或添加代码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软件测试过程,甚至通过在线公共论坛进行知识构建时,这种现象就变得很明显了。因为这些潜在的价值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这些空间不仅应该欢迎,而且应该积极鼓励来自不同人群的参与;然而,正如本文开头的讨论所显示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相反,对话合作的创作模式和数字空间中排斥意识形态的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结果往往是对抗或排斥的实践,这些实践积极地阻止这些空间在开发或包容性方面发挥其全部潜力。
开源软件(OSS)运动是大规模协作创新实践中最多产的例子之一。它对互联网空间中成长起来的开发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OSS开发的生产性与它的散漫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8148],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外文翻译、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